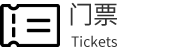源通三教花山庙
源通三教花山庙
乔文博
在花果山南天门村北的一片山坳里,摆布着一座千年古庙——花山庙。如果说花果山是一座西游文化名山,那么这里就是这座名山的灵魂所在。因为,西游文化的核心元素——齐天大圣孙佛崇拜,就集中体现在这座庙宇中。
先来看一下花山庙的殿堂布局。
受地形限制,花山庙的殿堂布局不像一般寺庙那样规整。它坐东向西,背靠玉皇顶,两侧被十八罗汉峰簇拥着,近二十座殿堂(据说全盛时期有百余间)分散摆布在一片芭蕉叶状的山坳里。蕉叶的中间,有一条山脊微微隆起,似可作为整个庙群的中轴线。最下端(叶柄处)是灵官殿,最上端(叶稍处)是玉皇殿,蕉叶中段有一片约略平坦的地方,则端端正正座落着整个庙群的核心建筑——西佛殿。乾隆十五年《重修西佛殿碑记》中记曰:“群峰拱绕,中有灵祠,人或谓孙大圣之祠也”,道光八年宜、新、渑三县香客曾募化银两,在殿内为大圣修造了精美的佛龛(见《建修齐天大圣木暖阁序》)。可见,作为花山庙核心的西佛殿,供奉的主神正是齐天大圣孙佛,而且礼遇甚隆,影响遍及周边各县。
齐天大圣“神通显于上古,归真原自唐代”(见上引《木暖阁序》)。这里说的“归真”就是“成佛”。成了什么佛?花果山人名之曰“西佛”。依《水经注》所说,汉明帝夜梦金人,问于群臣,对曰:“西方有神,名之曰佛。”这里说的“佛”,是神祇的一种,属群体形象。花果山人所称的“西佛”并非笼统的“西方”之神,也非释迦牟尼,而是有专指的“齐天孙佛”(见《花果山庙碑记》)。所以称孙佛为西佛,是出于一种原始的、朴素的认识。他们从传说出发,认为齐天大圣是在西天取经功德圆满后成的佛,自然就应该称作“西佛”了。至于小说《西游记》中如来佛祖在灵山会上当众所赐的“斗战胜佛”,则未必了解,亦或后来虽知道了,因此名来得晚,当地人且礼从其俗,仍以“西佛”相称,这当属“前西游文化”的一种表现。受花果山影响,把孙悟空作为“西佛”来敬奉的现象在宜阳相当普遍,如张坞七峪庙有西佛殿,韩城福昌阁有西佛洞,县城东关有西佛庵等,不一而足。
花山庙西佛主殿前,两侧偏殿分别布局着白衣殿(供观音)、伽蓝殿、悟祖殿(供猪八戒)、三祖殿(供沙僧)等殿堂。观音又称白衣大士,依《西游记》所写,观音菩萨在世间专施慈悲度人,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修成正果的领路人,但因仍是菩萨身(灵山会上唐僧、孙悟空在诸佛中分列第47、48位,观音则仍称菩萨,列名悟空之后),所以在此处只能屈居偏殿;伽蓝是佛教护法之神,安排在山门内第一进院落当属履职所需;猪八戒和沙僧在灵山会上仅获净坛使者和金身罗汉称号,属沙门内较低级别,未获佛号,但毕竟和已修成正果的孙悟空兄弟一场,在偏殿供奉倒也合乎情理。
沿花山庙西佛殿形成的中轴线向后延伸,还有许多殿堂。挨得最近且形制最完整的殿堂是十二老母殿,该殿捐棚、正殿相连,保存完好。当地百姓中流传着“悟空寻母”的故事:说是孙悟空修成正果后回到故里花果山,对自己石卵所生的出身很是伤心,想到当年被压在五行山下时,有一群老妇人常去探望,采摘野果让他充饥,顿生报恩之心,便认花果山一群老太太作了娘亲,朝夕供养。后人便据此传说在西佛殿后建了老母殿,提醒世人及时行孝。该殿还存有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所立的《重修十二老母殿并金粧神像碑记》,撰文者说,正因无由下笔“隐几而卧”时,“忽梦白发之妇十数人”对自己说,“吾辈居花果山,几历年所,其敬吾者伙矣”,并告诫说:“有能孝于亲者,即不敬吾而吾喜;有能慈于幼者,即不敬吾而吾悦。若夫孝慈两无而徒恃虔恪,亦何益哉?”撰文者深感梦中老妇的话“至言哉”,起而为文,碑文虽短,却发人深省。那些不孝于亲、不慈于幼的人,仅凭到庙里磕头烧香又有什么用呢。
老母殿后是老君堂,供奉被道教神化了的主神太上老君(即老子李耳)。再后是张氏母殿,据说所供是张玉皇的女儿七仙女,应该是道众造出来的一尊神,在花果山一带影响颇广。此殿后的三教堂已处于山坳中心山脊的前端了,三教堂中供奉佛道儒各路神祇,中间的三尊神:释迦牟尼居中,左右分别是孔子和老子(其实三者均实有其人,为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圣哲)。顺山脊再往上走是三官殿,供奉天、地、水三官。山顶处的玉皇殿,是整个庙群的最高处,供奉着在《西游记》中被尊为万神之王的玉皇大帝。
上边所述,是中轴线上排列的主要殿堂,多数已经善男信女重修。还有一些诸如奶奶、雷公、山神、土地之类的小庙,在山坳各处星散分布,稍显破旧。另有一些,如三清殿、玄武观、六祖庙 、(茅、衡)山庙等,则仅存残碑,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尚无人亦或无法恢复。“山高皇帝远”,由于管理松散的原因,近年来一些居民或自建、或集资修造了一些老母、财神之类的小庙,如果再加上此类似乎“非法”的建筑,整个花山庙群可称儒、释、道、俗群神毕至。在一片不大的山坳里,集中如此众多的神祇,堪称奇观。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华山庙是花果山西游文化的灵魂所在,而西游文化本身就是亦佛亦道亦儒亦俗的一种民间和民俗文化。(见拙作《西游文化三题》)
西游文化不等于《西游记》文化,但不可否认,《西游记》成书后,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西游文化并扩大了其影响,自然也包括滋生了西游文化的花果山在内。我们研究西游文化,自然也不能撇开《西游记》。
关于《西游记》,鲁迅先生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
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的游戏。只因为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迦、老君、观音、真性、元神之类,无所不有。使无论什么教徒,皆可随意附会而已。
鲁迅在此用了“游戏”二字,且不可产生误解。鲁迅的原意是说,《西游记》的“宗旨”(也即主题),决不是单纯的劝学、谈禅或讲道,因为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才会各路神祇“无所不有”,以便被各类人等接收。须知,小说在古代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直到清代在上流社会中也还得不到认可。但在市井坊间却很受欢迎,根据神话小说《西游记》改编的戏曲、话本在民间也很有市场。为了取悦听众,艺人们在演唱、评说过程中往往添枝加叶,说起石卵生猴、大闹天宫以及取经路上各路妖魔占山为王、霸洞成怪直到最后被成功收服的故事更是信手掂来,极尽想象、夸张、戏谑之能事,以便“无论什么教徒,皆可随意附会”,收到皆大欢喜的效果。有几分幽默滑稽的“游戏”笔墨,是此类市井小说惯常的表现手法。
说到《西游记》的题材特征,曾有研究者用“佛表道里儒骨髓”一句来概括(见《20世纪西游记研究》,2008年10月版,花三科文),我欣赏作者独特的视角,但不能完全赞同其结论。“佛表道里”很容易被理解为“表面上写佛、实质上写道”,实际上就其内容来讲,《西游记》一书中是佛道杂揉的,很难说哪方面分量更重。从作品中流露的倾向看,倒是对“佛”的推崇多,对“道”的贬损多。写佛时虽有一些“游戏”笔墨,如说如来是妖精的外甥、菩萨曾做过妖怪等,猪八戒最后的封号“净坛使者”也叫人忍俊不禁,这些不过是些小幽默;而写道时态度就截然不同了,许多地方显露着批判的锋芒。西游路上所遇到的“昏君”,多数都因信奉道教或受道人术士蛊惑而为国家引来灾祸。乌鸡国的全真道人、车迟国的“三力”仙长竟然是畜生所化,比丘国的道人残忍到要用小儿心肝做药引子。《西游记》成书当在嘉靖朝后(1565年后),联想到嘉靖帝(明世宗)的毁佛佞道以及他久居深宫不理朝政和迷信丹药乞求长生的种种怪诞行为,作者骨子里的“儒骨髓”批判锋芒所指,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花山庙的三教成分该怎样认识,我想可以将上引“佛表道里儒骨髓”这句话改个说法,叫做“佛主道辅儒精髓”。显然,以西佛殿为代表的佛教殿堂占据着最尊贵的位置,而其他道教和民俗诸神则如众星捧月般散居于上下或两侧。和《西游记》不同,花山庙虽然崇佛,却并不贬道,表现出对佛、道、儒、俗各路神明兼收并蓄、一视同仁的和谐景象。在古代交通不畅的情况下,花果山是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山民们既要防止野兽的袭击,也要防止盗匪的劫掠,还要抵御各种自然灾害,所以对神通广大的孙佛老祖敬爱有加是不难理解的。《重修齐天大圣孙佛老祖庙宇序》中称:“我孙佛老祖……神功浩大,灵应如响”;《重修西佛殿记》则称:“要之克御大灾、能捍大患者乃祀之”;而《建修齐天大圣木暖阁序》更明确指出:孙佛“神通显于上古,归真源自唐代,驱邪卫正,至今犹显赫耳”。可见山民们认为孙佛不仅能“卫正”(匡扶正义)而且能“驱邪”(扫除邪恶),这和一味讲善念佛、不许斩妖除魔的唐僧就大不相同,所以花山庙中只为悟空三兄弟建了专殿,却没有为唐僧留个位置。
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其理论系统的严密程度远不及佛教,其神祇系统更显得庞杂纷繁。早期的道教除以老君(李耳)为最高神外,还崇拜“三官”(天官、地官、水官),直到南朝道教理论家陶弘景出现后,才为道教编排了一个“三清”、“四御”等级分明的神祇体系。这个体系共分七级,其最高阶为三清,即玉清原始天尊(据说为盘古氏)、上清灵宝天尊、太清李老君。原本的最高神老子在新体系中已屈居第三,至于《西游记》中统帅各界的万神之王——玉皇大帝,则位列第九。但是,陶弘景的这个体系在普通民众甚至知识分子中知之者甚少。一提起玉皇大帝,在中国可以说是如雷贯耳,花果山百姓更是妇孺皆知,在花果山庙群中把玉皇大帝安排在中轴线的最高处。前边说过,《西游记》中对道人多有贬损,花果山人则礼敬如常,甚至还自造了一些神祇与之为伴。 不过,与对待齐天孙佛的态度相比,似乎略显逊色了些。就像他们将玉皇殿建到山顶上一样,看起来高高在上,却有几分敬而远之了。
花山庙中“儒”家作为宗教所占份额甚少,只在三教堂内为孔子塑了一尊像。但纵观整个庙群布局,却不难看出所体现的儒家精神。玉皇大帝高高在上,俯视着宇宙苍生,无论是道家的三清、四御,还是佛家的孙佛、菩萨,乃至儒家的孔老夫子,无不在其脚下俯首称臣。其中西佛殿和其后供奉的十二老母殿紧紧相连,又体现出一种母慈子孝的家庭伦理关系。《十二老母殿碑记》就是永邑(今洛宁)一个儒生所写,“有能孝于亲者,即不敬吾而吾喜;有能慈于幼者,即不敬吾而吾悦”这句话,简直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儒家经典的翻版。可见花果山庙群通过其殿堂摆布所要体现的正是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忠孝治天下的封建伦理,而这一点正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
儒、释、道三家所以能在花山庙和谐共处,还在于在思想上的同源。比如三家都讲“行善”:佛家讲发“善念”,修“十善”而成正果;道家讲“上善若水”,要像水那样“利万物而不争”;儒家则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写进了儒学经典。三家都讲“修心”:佛家讲“放心”(驱除杂念),主张通过禅修“明心见性”;道家讲“养神”,主张通过自身修炼达到“识心见性”;儒家追求“修齐治平”的价值观,其基础就是从“诚意(意念纯真)、正心(心思端正)”起步的。至于花果山百姓,倒不一定了解(或无需了解)这么多道理,但他们从对大自然心存敬畏出发,认为万物有灵,要广结善缘、积德祈福。所以在敬奉自己的保护神——齐天大圣而外,还为各路神仙都修了殿堂(尽管很小),而且笃信心诚则灵的古训,见庙烧香。
我向来认为,人知有所敬畏好,比如敬天畏地。敬天畏地、善待万物,爱护好生态环境,走绿色发展之路,也是当前新发展理念的题中之义。(4587)

 中文
中文 ENGLISH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