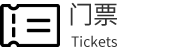西游文化论坛
您的当前位置:首页 > 西游文化 > 西游文化论坛
西游故事、传播、改写、小说文本的来历 研 究
更新时间:2021-12-10 13:07:55点击次数:1047次
与明代产生的人多数古典白话K篇小说一样,《西游记》亦导源于历史中实有之事。小说取材丁唐代僧人玄奘西行求法的史迹,在该小说正式成书之前,玄奘两游经历了故事的缘起、传播和丰富的过程。在这一历时久远、塑造者众多的成书过程中,不仅有民间艺人的讲唱言说,也有文人的踵饰其华,甚至还有宗教徒们的附会修撰,创造者们的这些改写百川汇流,最终使两游故事由一次中土佛教史上的壮举,脱胎换骨为想象奇幻、意蕴丰富的文学叙事。
西游故事、传播、改写、小说文本的来历
研 究
(原始材料汇编)
与明代产生的人多数古典白话K篇小说一样,《西游记》亦导源于历史中实有之事。小
说取材丁唐代僧人玄奘西行求法的史迹,在该小说正式成书之前,玄奘两游经历了故事的缘
起、传播和丰富的过程。在这一历时久远、塑造者众多的成书过程中,不仅有民间艺人的讲
唱言说,也有文人的踵饰其华,甚至还有宗教徒们的附会修撰,创造者们的这些改写百川汇
流,最终使两游故事由一次中土佛教史上的壮举,脱胎换骨为想象奇幻、意蕴丰富的文学叙
事。
玄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宗教家,是中十佛教唯识宗的开创者,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翻
译者,不过,最为tH=人所熟知和乐道的,是他去印度求取佛经的历险经历。在古代社会文化圈系相对封闭,人们惯于安土重迁,交通环境极其落后的条件下,玄奘白侦观三年秋起,“远
涉恒河”,“频登雪岭”,前后历经一十九年,广涉异域,从佛祖之地——天竺求取剑了“如
来之秘藏”、“释迦之遗旨”,最终返回东土。他的这一近乎“天路历程”的行为无疑可以称
之为一个奇迹,在世人眼中充满了神奇感,也延展了他们对陌生地理世界的想象。因此,从
玄奘两游故事的缘起之时,文本叙事便逐渐具有了神异传说的色彩。
关于这次两行求法的历史记录,首先是玄奘本人的各类表、启这样的零碎文本,简单勾
勒了自己西行的经历。此外,最早且最直观、完整的文本当属玄奘口授、弟子辩机撰文的《大
唐西域记》,以及其弟子慧立、彦惊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记
载玄奘西行所经过的各国的历史、地理、社会状况,既有各种迥异于中土的奇风异俗,也不
乏宗教传说的记载,特别是这些宗教传说,是以玄奘亲历发生之地的方式记载-卜.米。类似《犬
唐撕域记》卷一“迦毕试国”中,“城西南有比罗娑洛山,唐言象坚。山神作象形,故日象
坚也。昔如来在世,象坚神奉请世尊及千二百大阿罗汉。山巅有大磐石,如米即之,受神供
养”这样的叙述,反复出现,使得玄奘的西行求法之路,在读者眼中变成一次践履神迹之路,
玄奘本人乃至其西游经历因此有了神异的色彩。在稍后出现的玄奘传——《大唐大慈恩寺三
藏法师传》中,这种神化玄奘和西游故事的痕迹更加浓厚,玄奘得以度过漫长艰苦的取经历
程,与他作为信心执着的宗教信徒而时时受到神佛的保护,有莫大的关联。一次地理学意义
上的冒险故事,在玄奘弟子的夸饰敷衍下,呈现出一种趋向宗教理念宣讲的变形,取经路上
种种的磨难,遂被改写为神佛拯救的“幸运”,以强化信众的宗教信心。
这些讲述玄奘取经故事的历史文本,与后来的小说《西游记》也相去甚远。但作为小说
所依托的蓝本,还是为后来的文学叙事准备了条件。一是曲游故事中自马驮经的缘起。在玄
奘本人的表启一类的零碎文本中,尤可注意到的是玄奘屡次提及自己取经回来的过程是“白
19
马驮经”,《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有:“奘以贞观三年往游西域⋯⋯总获六百五十七部,并
以载于白马,以贞观十九年方还京邑。”又《谢御制三藏圣教序表》有:“搜扬三藏,尽龙宫
之所储;研究一乘,究鹫岭之遗旨,并以载于自马。还献紫宸。”等,白马驮经乃汉明帝时
事,洛阳白马寺由此得名,而玄奘多次讲述自己取经事用此典譬之,也就为后世文学叙事将
这两个历史事件的杂糅创造了条件;二是两游故事基本架构的建立。无论是《大唐两域记》,
还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都记录了玄奘西行求法之路所经过的西域诸国,在这两
个文本中,西域诸国虽还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描述,与后世的两游故事多为文学架空不同,但
遍历诸国度基本架构不变。中间所涉及的个别国家,仍为西游故事所承袭,如《大唐西域记》、
《法师传》中都有提剑的“两大女国”。三是神话色彩的讲述基调建立。玄奘西行求法,无
论是参与者还是记录者皆为佛教徒,其讲述肯定不同于一般旅行者所写的游记,超自然的宗
教叙述是其特点之一。故在《大唐两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两个文本中明显见
到宗教神话对玄奘西游这一地理旅行故事的渗入和改写,尤其是后者,多次记录了玄奘受到
畔申佛帮助的故事,《法师传》卷一有玄奘欠道野马泉,饥渴欲死,于沙中默念观音经,遂得
梦中神人指路,而获拯救事;卷三有玄奘于河上遇十余贼船,群贼欲以幺奘身体血祭突伽天
神,而玄奘受慈氏菩萨庇护,于是江面上“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
群贼折服受戒后,“风波还静”,以上都可以在后世的硝游故事上见到类似的影子。
除了以上三条要素间接影响剑后世两游故事的成型之外,历史叙述中的玄奘两行故事,
部分文本还直接深刻地影响到了文学的西游叙事,例如《法师传》中提及的《心经》故事。
这在下文中详细分析。
由唐末开始,一直到明中叶,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是唐僧西游脱离历史文本而逐渐向
文学的“西游”故事系统嬗变的过程,取经故事在宗教俗讲、造像、戏剧、平话、民间宗教
等渠道中传播,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嬗变过程不是单线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流传于受
众群体中的两游故事,并非干人一面,这些西游故事相互碰撞、相互借鉴,故事中的人物和
情节也因之渐次增加,逐渐发育成熟起来。
宋元时期,西游故事的传播开始向民间转移,寺院为了吸引民众,以“俗讲”的方式传
播一些宗教故事,以达到推,“宗教的目的,讲述玄奘两游的《人唐三藏取经诗话》便是其中
之一,由于《诗话》面向的接受群落,多为文化不高的俗众,故需要对原有的玄奘两游进行
加T和重写,删汰掉写实的游记色彩,而着意丁故事的奇幻效果和市井趣味,西游故事开始
脱离历史讲述的樊篱,具备了文学虚构的特点。《诗话》的奇幻效果是通过引入神魔形象和
神魔世界而达到的,与《两域记》和《法师传》不同,《诗话》中出现了人量的超现实的元
素,如火梵天王、王母、定光佛等神仙以及于深沙处横行吃人的深沙神、变成白衣妇人的白
虎精、九龙池处的九条馗头鼋龙等妖怪。最引人注意的,当然是《诗话》版本的西游故事对
玄奘一行人进行了改写,在取经队伍中安插了一位神通广大的猴行者,帮助玄奘降妖伏魔,
这标志着孙行者形象的正式出现。此外,《诗话》还通过对玄奘两行所经历的诸国进行重写,
变历史地理中实有之诸国为想象虚构的国家,如化用佛教中鬼子母之传说,创造出鬼子母国;
将玄奘西行时没有经过而仅提及一笔的“西大女国”,演绎为女人国,并编排了女人国国王
爱恋玄奘,却被其所拒的故事等,这也使玄奘西游由历史向超越的、想象的世界迈进了一大
步。
如果说《诗话》与之前的玄奘故事,还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只有玄奘本人了。但是即
便是这同一人物,由于改写者心态的变化,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历史中的玄奘坚韧执着,
几乎独自挑起了所有的困难,而《诗话》中的玄奘,既有大梵天王所赠的三宝:金环锡杖、
隐形帽、钵盂,又有猴行者的帮衬,更无危险艰难可言,所以,他的性格特点被削弱了不少。
不仅如此,在王母池处,玄奘竟然命令猴行者偷桃,看其所言,先是建议行者:“何不去偷
一个?”猴行者担心被捉,其又宽慰:“你神通广大,去必无妨。”至听见桃子落水时,则命
20
令道:“可去寻取来吃。”活脱脱一馋鬼的形象。由此也可知,在向民间传播的过程中,市井
趣味开始渗透到两游故事中来,并影响到了人物的塑造山。
宋元宗教人士向民间传播玄奘西游故事,并不J卜于俗讲这一渠道,还借助于造像艺术,
据已发现的资料,敦煌安两榆林窟保存有六幅两夏时期的唐僧取经壁画;杭州飞米峰龙泓洞
口,有据称成于元代的两组唐僧取经浮雕;广东省博物馆馆藏元代磁枕上,亦绘有唐僧取经图
等。出现于元代中期的《唐僧取经图册》更是以系列图画讲述了玄奘两游故事罾,包括了“张
守信谋唐僧财”、”毪虎国降大、小班”、“五方伞盖经度白蛇”、“玉玑夫人”、“释迦林龟子夫
人”、“六通尊者降树生囊行者”、“金顶国长爪大仙斗法”、“哑女镇逢I亚女大仙”、“明显国降
大罗真人”、“悬空寺过阿罗律师”、“过截天关见香因尊者”、“篮尉见摩耶夫人”、“白莲公主
听唐僧说法”、“万程河降人威显胜龙”等《诗话》中没有的内容。尽管有诸多不同,《图册》
早现出对玄奘两游进行神魔化重写的意图,却是与《诗话》一致的,两者另一相似的特点是
受到了密教的影响,毗沙|’J天-干都是作为玄奘的护法神山现的,《图册》中毗沙J、J天千护法
的作刚尤其明显,其地位相当于后期小说《两游记》中的观世音:落萨。
宋元时期,通俗文艺登上舞台,唐幺奘西游故事作为神鬼题材吲,自然也会得到诸如戏
剧艺术、说话艺术等通俗艺术门类的青睐。宋代之后,两游戏开始出现在戏剧舞台上,现在
已知的有,宋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唐三藏》、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两天取经》
等,这些戏剧或铺陈故事,或择其片段演绎之,其中情:1,最完整全面的,当属杨景贤的《西
游记》杂剧。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产生元末,较之作为宗教宣讲的两游故事,戏剧更注
重营造故事的吸引力,唐僧一行人,已经由普通凡人彻底过度到了神魔组合,唐僧陈光蕊乃
两天毗卢伽尊者托化,徒弟猴行者是大闹天空的“通天大圣”,“铜筋铁骨,火眼金睛”;朱
八戒是摩利支天菩萨座下的猪妖;沙和尚是玉皇殿前卷帘人将下凡。在故事架构上,孙行者
地位提高,几个主要的关口,收拿沙和尚、猪八戒、借铁扇、黄风山等,克服凼难的主角都
是他,说明西游故事的侧重点开始由唐僧取经向行者伏魔方向转变,其形态已经比较接近小
说《西游记》了。
杂剧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已完全市民化了,唐僧变成了一个性格软弱,屡受妖魔侵害,
需要神佛和徒弟时时加以保护的书生,遇剑火焰山阻隔,便叫:“来至火焰山,如何得过去,
行者怎生是好?”女人国被国干所迫,他先大叫“孙悟空救我。”见行者被缚,又对天大叫:
“谁来救我!”等,完全是一副无能、无主见的面孔;唐僧的儿个徒弟,则多少带有了点市
井无赖的色彩,女儿国唐僧脱难后,质问几个弟子为何不救自己,行者的答言可以说是这种
市井趣味的最生动的表现:
(唐僧云)行者,我们十分亏神天护持,脱了此一难。我且问你,我吃女王拿住,
你每三个怎的脱身?(行者云)师父,听行者告诉一遍:小行被一个婆娘按倒,凡心却
待起。不想头上金箍儿紧将起来,浑身上下骨节疼痛,疼出几般儿蔬菜名来:头疼得
发蓬如韭菜,面色青似蓼牙,汗珠一似酱透的茄子,鸡巴一似腌软的黄瓜。他见我恰
似烧葱,恰甫能忍住了胡麻。他放了我,我上了火龙马脊梁,直走粉墙左侧。听我有
个曲儿,唤做【寄生草】:
o《诗话》“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几处第十七”讲后妻谋害前妻之子事,曲说世情,也折射出市井之趣
味。
罾《唐僧取经图册》最早为日本学者矶部彰等学者所关注,并有相关研究文章,国内新近研究这一
图册与西游故事关系的,为曹炳建先生,参见其《((唐僧取经图册)探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8年第6期。
∞通俗艺术对神鬼题材的喜爱其来有自,宋耐得翁《都城纪胜》中讲:“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
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人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足也。”吴自牧
《梦粱录》中则说:“凡傀儡,敷演炯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
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皆指偏爱的主题中即有烟粉灵怪这一类神鬼故事。而元代杂剧中,神仙
道化、神头鬼面也是戏剧的两个重要题材,见明人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对元杂剧的分类。
21
【寄生草】猪八戒吁吁喘,沙和尚悄悄声。上面的紧紧往前挣,下面的款款将腰
肢应。我端详了半晌空侯幸,他两个忙将黑物入火炉,我则索闲骑白马敲金镫.
这种粗俗、黄色的描写也只有在市民意识占主导地位的通俗文艺中才能出现。
除了杂剧之外,其时还流传有一部《两游记》平话,平话《两游记》现已亡佚,不过仍
能从一些零碎的记载中见其人略。《永乐大典》尚存“梦斩泾河龙”一段故事;古朝鲜的《朴
通事谚解》中则载有“车迟国斗圣”的故事,在注解处详细介绍了西游故事的主要内容:“初
到狮陀国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经、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
孩儿怪,儿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水⋯⋯”这两部书都
将所摘择的故事来源标为《西游记平话》。透过这些零星的记载,可知平话《西游记》作为
叙事文学文本,故事情节基本完整,将其称之为小说的底本或蓝本,毫不为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间宗教的兴盛也推动了两游故事的传播,特别是明代,罗教、黄
天教、东西大乘教、弘刚教等民间教派叠次出现,这些宗教借助通俗文艺,传播教理,吸引
信众,因此在民间宗教教典——宝卷中留有大量的叙事文学素材,象《伏魔宝卷》谈的是关
帝;《二郎宝卷》则是二郎神;《东岳天齐宝卷》的主神自然尔岳大齐人帝;《地藏十千宝卷》
涉及佛教地狱的传说等等。但没有一个故事素材有唐僧两游故事这么大的影响力,明代主要
民间宗教,如罗教、黄天教、西犬乘教、红阳教、圆顿教等等的宝卷中都有两游故事的影子
∞。由于宝卷中的曲游故事是某些民间宗教宣传家用来传道的媒介,所以,呈现出宗教譬喻
的特点,这与在其他传播渠道中流行的两游故事是不同的。
玄奘西游故事由历史传记逐渐演变为叙事文学,这个过程呈现一个世代累积的特点,一
方面故事通过俗讲、通俗文艺等各种渠道散播于民间,另一方面不满足于接受已有故事的受
众,出丁这样或那样的目的,也会依据自己的期待视野进行发挥,改造故事以契合自己的思
想或审美需要,因此不同身份的作者,参与到加一F、改写中来,故事在I同有形态的基础上不
断地丰富,文学性、趣味性也不断增加。西游故事的基本形态便在这种动态的、复杂的传播
互动关系中逐步成熟。传播、接受的复杂性相应地造成了西游故事文本素材来源的多样化,
这主要体现在旧素材的复述改写,新文本和新文化因素的渗入等,尽管由于相隔久远,已无
法完全描述出这种文本互动的原貌,但仍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窥见一斑。
首先是文本的复述改写,《心经》故事是典型的一例。《心经》与西游记故事之间的缘分,
可上推至唐代。中国古代翻译《心经》的,较为有名的有两人:一是南北朝时期的鸠摩罗什,
另一个就是唐玄奘,唐玄奘所译《心经》,也即《两游》所引之《心经》,以文字简洁明晓而
广受欢迎,取代了鸠摩罗什《心经》大行天下,后人所用皆其译本。这也大概就是玄奘弟子
们把西游与《心经》编在一起的原因,《法师传》卷一讲述玄奘过“长八百余里”古沙河时: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孤影惟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
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与衣服饮食之直。病者惭
愧,及售法师此经,因常诵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
①最早传播西游故事的是,正德年问出现的罗教,此后嘉万年间的黄天教祖师普明即以西游故事作为传教
之丁具。《佛说利生J,义宝卷》之“戊午开道普明如来归宫分第十三”“普叫佛,为众生,投凡住世;化男
身,性木子,四十余春;聚fE门,为结发,开花一二朵;长聘康,次聘高,两氏夫姻;有如来,再不知,已
为佛体;边塞.f:,受尽了,苦楚官刑;戊午年,受尽苦,丹书来召:大开门,传妙法,说破虚空;炼东方,
甲乙木,行者引路;炼南方,丙丁火,八戒前行;炼北方,壬癸水,沙僧玄妙:炼西方,庚辛金,白马驼
经;炼中方,戊巳土,唐僧不动;黄婆院,炼就了,五帝神通。”戊午为嘉靖三十七年。尽管其他的民间
宗教教派如弘阳教、东西大乘教等的产生,晚于小说《西游记》刊行的时间,但j£教派内部流行的西游故
事形态与小说小同,保留丫之前两游故事的形态,考虑到民间宗教相对封闭的体系和前后承袭的特点,认
为这些教派内的两游故事早于小说的出现,当不为过。
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
这一段文本素材,因其强调持经信心的神异效果,又刻意凸显《心经》祛邪的作用,为玄奘
故事的接受者所注意。
最先对这一素材进行复述和改写的,是唐末以后《独异志》等这样的笔记小说,复述
和改写的趋势,便是授经之人来由以及《心经》法力的神化,授经之人由《法师传》中感激
玄奘救助的“病人”,变为《独异志》中厕宾国道上“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却莫知由来的
老僧,《心经》的神奇效果一并夸饰为“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
但从叙事的内在逻辑上,《独异志》等志怪小说的《心经》故事与《法师传》差别不大,都
强调了《心经》在玄奘西游路上的保驾护航的作用。《独异志》的叙述后被收入《太平广记》
中,为世人所熟知。毫无疑问,这一授经的细:肖被小说《西游记》创造性地吸收进去哪。
至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心经》授受故事被编写者进行了较大改动,《心经》
的传授者不再是乞丐,或者来历不明的奇僧,演化成地地道道的神祗定光佛;《心经》保驾
护航的法宝功能也消火了,成了幺奘两行所要取的经典,且此经地位不凡,是在幺奘取得五
千四十八卷经文后,由定光佛单独传授的。正冈如此,这部经书才与玄奘历经艰辛所取得的
其他经书截然不同,“此经上达天宫、下管地府,阴阳莫测”,有着出类拔萃的神奇作用,东
土薄福之人,难以承受,故定光佛特意强调玄奘“慎勿轻传”,明代的民间宗教流传的某些
两游故事,强化了《诗话》的这种叙述结构,主要体现在《心经》取代了五千四十八卷其他
经文,成为唐僧一行取经的最终成果,“经历千山万水,受过若干魔障,方到雷音寺,取得
一卷《心经》,来到东士,超度亡灵,得升净十”;《诗话》中非凡俗薄福之人所能接受的《心
经》,则干脆被民间宗教命名为神秘的“无字经”。有意思的是,在小说《IHi游记》的结尾处,
有一段唐僧师徒取错经文的叙述,作者借此讽刺了某些佛教徒的贪财之相,但其中反复强凋
东土众生愚迷不悟,不识无字之经,与《诗话》系统的《心经》故事倒是颇有几分神似之处。
不排除《西游记》作者也承袭并改写了这一素材,纳入剑自己的小说文本系统中的可能性。
《心经》故事的传播及改写,使得这一情节具有了丰富曲折的变化,为小说《西游记》
的创作者处理这一西游故事的同有素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是新文化冈素、新文本的渗入。例如我们熟知的斩泾河龙、太宗游地府、陈光蕊江
流和尚等,起源之初皆属独立的故事系统,只是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渐次“参与”到西游
故事主体里来学。应该说这些新文化因素和新文本对于小说人物的产生、形象的丰富、情节
的拓展影响颇大。
两游故事从产生之日起,便置身子宗教信仰系统之中,记载玄奘西行的历史传记本属佛
教系统的文本,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虽已摆脱了历史传记,具有文学虚构的特点,
但作为俗讲,宗教色彩依然浓厚,密教成份的掺进是一显著的特点,沙和尚的前身深沙神是
从密教中实有的神祗——深沙大将借来的,唐中叶即有密教僧人不空所译的《深沙人将菩萨
仪轨》@,可知此一神祗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当然,《诗话》还吸纳了一些本士道教的
神仙故事,东方朔偷窃西王母蟠桃被讲述者改换了面目后,运用在了叙事中,说明宗教冈素
的杂糅,在西游故事传播的早期就已经开始了。元明之际的西游故事,本十道教强势介入,
宗教杂糅的趋势更加明显,以杂剧《西游记》为例,一些角色残留有密教的影响,如托塔李
天王,尚保持着“毗沙门天王”的名号,剧中朱八戒为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其身份
与猪的形象皆源出密教㈤;但道教化神祗出现的密度大大增加,如在道教侵润下而“转投门
o《太平广记》对玄奘两游的叙述,是牵合了《独异志》的《心经》故事及《唐新语》的摩顶松两迎玄奘
之事,后者亦出现在小说的文本中。
o见胡适《两游记考证》七。
@此一密教神祗与玄奘两游结缘,最迟不晚于中晚唐,同本入唐求法的僧人常晓云:“右唐代玄奘三藏远涉
五天,感得此神。此是北方多闻天上化身也。”,常晓开成三年到的中国,撰有《将来日录》。
@当然随着故事的发展和定型,猪八戒也转换了身份,其出身变成J,“知名”的道教护法神——天蓬元帅。
户”的沙和尚,由密教的深沙大将变成道教玉帝殿下的卷帘大将;再如铁扇公主首次出现在
杂剧中,她住的山,名日铁嵯峰或铁嵯山,使一柄铁扇子,重一千余斤,威力巨大,“着扇
扇翻地狱门前树,卷起天河水波”,这一形象并非作者独创,宋元时期道教雷法中有“铁扇
符”,由此符之描写可见当时一些道教徒信奉“铁支罗汉圣母”,此圣母居住于铁茶山,惯使
千斤铁扇,“扇山山崩,扇石石裂”,杂剧中铁扇公主这一新角色,应是化自于宋元道教神祗
“铁支罗汉圣母”。宗教神祗不断地进入西游故事,显然是冈为其超自然的神通力契合了神
魔故事对于角色的要求。这与其他类型小说的人物产生是截然不同的。
一些文本的进入和杂糅,对故事的人物形象向立体化发展也起到了推进作用,这在孙行
者形象的发展上体现得十分鲜明。从产生之初形象单薄的猴行者,到大闹天宫、降妖伏魔的
孙行者,其间经过了众多环节的加上塑造,其中一个环节是白猿精形象的糅入,唐传奇《补
江总白猿记》所记猿猴夺女之事,至宋时被敷衍成道士伏妖的故事∞,宋话本《陈巡检梅岭
失妻记》详细地叙述了白猿的来历,“且说梅岭之北有一洞,名日申阳洞,洞中有一怪,号
日白申公,乃猢狲精也。弟兄三人:一个是通大人圣,一个是弥天大圣,一个是齐天人圣。
小妹便是、泗洲圣母。这齐天人圣神通广大,变化多端,能降各洞山魈,管领诸山猛兽,兴妖
作法,摄偷可意佳人,啸月吟风,醉饮非凡美酒,与天地齐休,日月同长”这个两游故事系
统之外的齐天大圣白中公,后来被改写者加工,附会于猴行者的形象之上圆,创造出了杂剧
《西游记》中的通大人圣孙行者,他的家族也更加扩大,计有:“小圣弟兄姊妹五人,大姊
骊山老母,二姊巫枝祗圣母,大兄齐天大圣,小圣通天大圣,三第耍耍三郎”。白申公故事
的引入和创造性加一I==,使得此一时期的孙悟空形象“劣迹”更加卓著,既有《诗话》猴行者
盗取蟠桃的事情,也有向申公夺女之恶行,不仅如此,还添加了盗酒盗丹、闹反天宫之事。
作为主要角色,其“资历”之丰富,是之前西游故事中形象苍白的猴行者所雄相比的。
人物角色之外,新故事素材的进入,丰富了原有的叙事。兹举一例,两宋间,道教系统
中存在着搜山拿妖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主要为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固,自宋初李益据此题材
做《搜山图》,后世画家临摹、仿做者甚多,这一故事也逐渐剥离了宗教色彩,成为文学性
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朝代的二郎搜山故事虽小有差别,但不少题画的诗赞皆提及妖
怪的一方出现有猴精,诸如“洞中果熟邀申公,笑擎饯耸倾云腴”(元代文人叶森题宋于辉
画《搜山图》五十韵),“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明吴承恩《二郎搜山图歌》),
“狙公醉倒笑语扶,我冠堕地犹狂呼”(清赵执信《题搜山图》)等,天兵临近,大难临头,
猴精依然醉生梦死∞,与之对应的是二郎神率领天兵天将四处拿妖的气势,“清源真君颜如玉,
回宋道:}:撰《温太保传补遗》记载了一个故事:蜀口有一县,猴神作祟,县宰率兵杀猴神,破其庙。后县宰
解官而回,为猴神报复,猴神变作县宰之像,夺其家,占其妻妾。县宰后得龙虎山虚靖天师所助,请下神
祗温元帅降伏了妖猴。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似为《补江总记》与这一道士伏妖猴的故事杂糅改写而
成。
岱杂剧《西游记》的通天大圣孙行者,还保留着《诗话》的某些痕迹,如其所居住之地为“花果山”“紫云
罗洞”,显系“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乇”演化ffli来,可见两个系统故事合流的痕迹。关于白
猿故事文奉与孙悟空之间的渊源,可参考台湾郑明蜊《西游记探源》第_二章“人物与故事的演变”涉及孙
悟空的一节,另孙悟空形象的米源之一是亡J猿精,还有一旁证,明郑之珍《新编日连救母劝善戏文》中,
保取经僧傅罗卜西行求法的即足白猿精,也曾偷上母蠕桃,后被观音所派的神仙收服,劝其保护取经僧。
《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中两游故事就成熟状态向言,似应在小说《西游记》成型之前。对此故事年代
的判断依据,可参见苗怀明《两套西游故事的扭结》,《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l期。
@搜山故事的主角,清源真君二郎神之外,还有崇宁真君关羽,只足后者小甚流行罢了,据名号可知,此二
人皆道教系统之神祗,谳搜山故事的产生可能与当时兴盛的道教降妖术有关,《泰玄酆都黑律俄格》之“邪
精品”云:“今山源古树中,或狐猴蛇虺藏其中,年深亦能变化荚貌才男少女,迷惑移运。法官宜奏紫微天蓬,
用威猛大将剪除之。”搜山拿妖应足掌握符策、雷法之术的道七法官们的本职工作,而在道上命令天蓬大帅
属下众神拿妖时,有“(群妖)或飞走pq散。变化逃遁,即仰学谷入山,搜岩破穴,仔细搜寻,尽数峻食,无致遗
类。其有伏法受擒者,并奉犬仙法旨,押赴天-:It;狱,依律治罪”(《上清天蓬伏魔大法》)文字,其状与-N搜
山无异。
④现保留于故宫博物院的南宋佚名作者所绘《搜山图》残卷,也有猿精的形象,不过此猿精已被鬼卒捉拿,
24
玉冠上服笼绣襦。座中神色俨而厉,来征水衡校林虞。文身锦膊列壮士,挟弓持弹金头奴,
烈烈勇气增垣赫,飞捷喏奏传献俘。”(叶森题《搜山图》五十韵)这一场面的营构充满了戏
剧的张力。搜山故事后来被改写,与猿妖齐天大圣的故事扭结在一起,典型如杂剧《二郎锁
齐天大圣》锄,杂剧《西游记》中的天王父子搜山,也当视为此故事的另一版本,这可从天
王吩咐哪咤“与眉山七圣大搜此山”中见出,眉山七圣本为二郎随从之将。搜山擒妖题材的
出现,强化了西游故事中悟空本事的戏剧性冲突。
西游故事的成型阶段还可能有过一个宗教徒以性命修炼思想比附两游故事的环节。最早
揭橥两游故事有宗教心性意涵的,是明弘治、嘉靖年间的文人孙绪,其《沙溪集》卷一五有:
“释氏相传唐僧不空取经西天,西天者,金方也,兑地,金经所自出也。经来自马寺,意马
也。其日孙行者,心猿也。这同打个翻筋斗者,邪心外驰也。用咒拘之者,用慧剑止之,所
谓万里之妖一电光也。诸魔女障碍阻敌,临期取经采药魔情纷起也。皆凭行者驱敌,悉由心
所制也。自马驮经,行者敌魔,炼丹采约全由心意也”,此段文字至晚不会超过作者去世的
嘉靖二十六年,早于己知《两游记》最早的刊本世德堂本四十五年。西游故事是孙绪“阏与
方外友谈之flip而特意记录下来的,所谓方外之人,即是道教修炼之士。由此可知,《西游记》
正式刊行之前,故事形态在流传过程中得到了道教徒“青睐”,并建构起了故事人物一宗教
理念的隐喻系统。这也能从嘉靖万历之间的民间宗教处得到证明,如嘉靖年间之黄天教《普
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锁心猿合意马,炼得自乾。真阳火为姹女,妙理玄玄,朱八戒按南
方,九转神丹;思婴儿壬癸水,两意欢然,沙和尚是佛子,妙有无边。”再如万历初年之《普
静如来钥匙宝卷》:“唐僧非上两天去,一灵真性走雷音⋯⋯我性即是孙悟空,白马原来是我
意,八戒原来是我精,沙僧原来是我命,五气聚足发卷经。”
应该说,西游故事文本提供了宗教徒进行这种比附的可能:两游故事产生、发展、成熟,
人物和情节吸纳了大量的宗教元素,本就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取经队伍中同时出现猿猴和
自马,契合了宗教修炼体系中的“心猿”“意马”之说,杂剧《两游记》中便有“着猢狲将
心猿紧紧牢栓系,龙君跟着师傅呵把意马频频急控驰”,恰可说明故事角色和宗教术语之间
的对应关系,非是后人强行比附所致;孙行者盗取金丹之事,在宗教修炼之士眼中止是“休
纵心猿,盗了金鼎还丹,谩劳虚费”(元冯尊师《苏武慢》之一)这一修炼思想的反证:而
禅宗六祖慧能强调自心即佛,西天十万八千里,即是内心修炼所面临的“十恶八邪”,这种
化地理路径为内心理路的象征手法,影响了后世的宗教修炼者,元全真道士混然子有诗:“西
天十万八千程,要到端然坐是行。诗句唤同担板汉,点开脑后眼分明。”对于秉持这种“前
理解”的宗教徒来说,唐僧两天取经简直是一个进行宗教化阐释的天然素材。等等。
总之,新文本新故事素材的改写揉合,在叙事层面上极大地充实了西游故事的内容容量,
让角色的面目更加生动形象;在哲理成面上使西游故事的意蕴变得更加复杂,多少带有宗教
象征的特征。没有经过这一过程,就没有今天所见到的神魔小说《西游记》。
=:
小说《西游记》究竟出现于那一年,现已不可考,现存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刊本是明万历
二十年金陵世德堂刊刻的《新刻出像官板犬字两游记》,所以,以世德堂本《西游记》作为
西游故事定型的代表,当不为过。
挑于枪上。其故事性没有元明清题画诗赞形容的f富。
回(--fig神锁齐天大圣》收于明赵琦荚辑《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创作的年代不详,大致可以推断为万
历之前,杂剧中齐天大每保留J,猴精家谱,弟兄姊妹五人:大哥是“通天大圣”,老二是“齐天大圣”。兄弟
是“耍耍三邮”,姐姐足“龟山水母”,妹妹足“铁色猕猴”,与杂剧《西游记》相类,而截然不问于小说;
另杂剧中二郎神“俗姓赵名煜,幼从道士李班,隐于青城山。至隋炀帝,知吾神人贤,封为嘉州太守。郡
左有冷源-二河,内有键蛟,春夏为害。吾神持刀入水,斩蛟而l叶j。後弃官学道,白曰冲升,加哥神清源妙
道真君”,尚为道教系统中的神祗,也绝不同于小说中杂入民间传说的杨二郎形象,故可推知此故事所流传
之年代与杂剧《西游记》接近。
与之前的西游故事相比较,定型后的小说《西游记》最大的不同之处,乃在于成书者创
造性的改写。关于这个最后的创作者,从最初的“不知其何人所为”,到清人提出的丘处机,
再到今人力推的吴承恩等,说法不一而足。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创作者一定是一位颇具
才华,“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且生性诙谐的文人。否则,小说《西游记》很难让“底本”
故事蜕变为充满叙事魅力的文学精晶。
首先,创作者在进行最后的加工创造时,有自己的意义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主导了
小说形象的塑造和结构的处理。主要体现在孙悟空形象上,尽管到了通俗文艺阶段,孙行者
在叙事中的分量已经大为增加,但尚没有取代唐僧作为取经队伍第一主角的地位,而在小说
《西游记》中,孙悟空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主角,取经队伍中唐僧、猪八戒、沙和尚三人的出
身经历,皆以诗赞的形式粗陈其梗概,只有孙行者,创作者单独为他敷衍了七同文字,巨细
无遗地介绍他的出生、求法、除混世魔王、龙宫寻宝、地府除名,官封弼马温,大战李天王,
受招安封齐天大圣、偷桃偷酒偷丹,赌斗二郎神、老君偷袭成功,八卦炉中炼人圣,再反天
富,被压五行山等一系列经历,不仅在情一肖的丰富上远超杂剧,更重要的是创作者借助这么
人的篇幅,对这一妖猴形象进行了全新的重塑,把一个市升气流氓气十足的无赖猴子,转化
为追求自由、心高气傲的英雄。创作者增加学艺求法、龙富取宝、地府除名的情节,其目的
是为了渲染行者“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渴望打破一切束缚的自由精神;增加招安的
情节,意在表现天庭所代表的规范、教条和行者不服天地管束之间的矛盾,为后来行者偷酒
偷丹大闹天宫,做了一种合理的说明,从而消减了猴妖形象同有的贼性,赋予行者争取自由、
反抗束缚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在细二钳上,创作者对行者的言行也做了颠覆性的修改,杂
剧中的通天大圣,面对天兵,只会说:“小圣一筋斗,去十万八千里路程,那里拿我。我上
树化做个焦螟虫,看他鸟闹,把我媳妇还丁本国,我依旧入洞,顶上洞门,任君门外叫,只
是不开门。”形象猥琐而奸猾;小说中的孙行者面对天庭的玉帝如来,却敢于宣称:“冈在凡
问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大。凌霄宝殿非他有,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
此敢争先。”透露着掀翻天地一往无前的气魄。小说《矾游记》创作者花如此大的笔墨去重
塑行者形象,正体现了创作者把自己追求洒脱自由的情怀和浪漫的英雄情结,寄托在了这一
人物形象之上。
其次,创作者有自己一贯的叙事态度,即一种轻松幽默的游戏心态。这种叙事心态是如
此明显,以致于任何时期的阅读者都能真切地感到,即便是那些试图从中找到微言人义的阅
读者也不能否认小说的叙事者“其意虽游戏三昧,而广大具焉”(《西游真诠》尤侗序)。而
这也造成整个叙事文本始终保有一种谐谑笑虐的美学风格。通观小说,除了游离于叙事之外
的同目和诗赞,上至神佛帝王,下至山怪妖精,无一不是其调侃捉弄的对象:道教的最高神
祗三清,被猪八戒仍进茅坑;佛教最高神如来佛振振有词纵容徒弟收受贿赂;朱紫国国王被
含有马尿的药医好等等。小说中一个非常经典的情节处理,充分体现了创作者的游戏心态。
僧人授《心经》的片段是西游故事系统固有之素材,自《法师传》有此一说,后被文言小说
作家改写后,广为人所知,小说《西游记》承袭了禅僧授经的情节片段,除了将《心经》的
授予权交给了一位历史上实有的禅僧——鸟巢和尚,全文还摘录了《心经》的内容,有意思
的是,就在鸟巢禅师授予《心经》,并信誓日.旦地保证“若遇魔障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
害”之后,唐僧曲行路上即逢妖魔,创作者是这么叙事的:“三藏才坐将起来,战兢兢的,
口里念着《多心经》不题”,“路口上,那师父止念《多心经》,被他一把拿住,驾长风去了”,
三藏对《心经》护身的依赖和妖魔捉拿的轻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衬托出唐僧此举的滑稽
可笑。更妙的是,两件事情前后衔接,一个在十九同末,一个在二十回初,可谓鸟巢的保证
言犹在耳,《心经》立刻就表现出无用之物的本色,足以见出创作者是有意而为之的,其目
的就是颠覆传统《心经》授受故事的神圣性。正是这种游戏心态,使得叙事文本始终处在一
种笑谑诙谐的氛围之中,读者从中所见到是神佛身上折射出的人性的缺点,那些严肃神圣事
物的滑稽荒谬,正如胡适所言:“《西游记》所以能成世界的一部绝大神话小说,正因为《西
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之开口一笑,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过了。”
最后,创作者有一个能够驾驭各种素材,并夺其胎,换其骨,最终点铁成金的文心。故
其笔下故事链条首尾完整,叙事空间奇幻瑰丽、人物情:肖鲜活生动,充满了艺术之美。以人
物塑造为例,小说《西游记》与杂剧、平话比较起来,主要人物角色无甚变化,但角色内涵
之丰富却远逾之,皆为极富亲和力的艺术形象。孙悟空的尊性高傲本性刚强,猪八戒的贪婪
好色义有些呆气,唐三藏的软弱怯懦等,主要角色无一不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
各有身份。这得益于创作者抓住形象的某些特点进行夸张渲染的手法。如第三十二回“平顶
山功曹传信莲花洞术母逢灾”有一段猪八戒巡山的叙述:
那呆子入深山,又行有四五里,只见山凹中有桌面大的四四方方三块青石头.呆子
放下钯,对石头唱个大喏。行者暗笑道:“这呆子!石头又不是人,又不会说话,又不
会还礼的,唱他喏怎的,可不是个瞎帐?”原来那呆子把石头当着唐僧沙僧行者三人,
朝着他演习哩。他道:“我这回去,见了师父,若问有妖怪,就说有妖怪。他问甚么山,
我若说是泥捏的,土做的,锡打的,铜铸的,面蒸的,纸糊的,笔画的,他们见说我呆
哩,若讲这话,一发说呆了,我只说是石头山。他问甚么洞,也只说是石头洞。他问甚
么门,却说是钉钉的铁叶门.他问里边有多远,只说入内有三层.十分再搜寻,问门上
钉子多少,只说老猪心忙记不真。此间编造停当,哄那弼马温去!”
之前八戒屡次偷懒,皆被悟空变化捉弄,己颇为狼狈,又想耍心眼蒙骗唐僧孙悟空,此处,
叙事者特意设置了他对着人青石拿腔拿调地编假话的场景,对着石头编假话本就荒唐可笑,
在外人眼里“可不是个瞎帐”,而八戒却浑然不觉,斤斤计较于把谎话编圆,让人莫笑话自
己呆,这种反差产生了强烈的滑稽效果,八戒的呆气跃然纸上。如此精心地运用情节来打造
人物的个性,无论是宗教徒,还是民间艺人,都雉以做剑,只有倾心于叙事艺术感染力的文
人,方能有此文心文眼。
由丁成书者创造性的改写,《两游记》最终成为一个故事架构完整、情节生动有趣,人
物角色性格各异,拥有强烈叙事魅力的文学作品。这样一个文学精品的出现,标志着晴游故
事传播演化进程的上E式结束,开始进入以小说《西游记》为对象的文学传播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止因为小说《两游记》并非文人的独立创作,文本中还保留了一些旧有
的痕迹,最突出的是定型后的小说文本,在叙事之上附着了丰富的宗教文字:一些来自宋元
全真道十诸如紫阳真人张伯端、全真教教主王重阳,以及元代全真道十冯尊师等人所做的诗
词;一些出自宗教修炼体系的文本,像小说第三十六回悟空以月象变化为譬,阐明“先天采
炼之意”,实是张伯端《蟾光图论》相关论述的简约浓缩版;诗赞和目录中存在大量的宗教
术语,包括了“灵根”、“心性”、“悟彻菩提”、“元神”、“定心猿’’‘‘意马收缰”“尸魔”“木
母”“真性”“旁门~‘金木”“金丹”‘婴儿~‘禅心”“猿马”“刀圭”“法身”“元运”“车力”
“脊关”“外道”“水火”“炼魔”“黄婆”“寂灭”“七情~‘阴阳窍”“真如~‘姹女”“金公”
“灵元~‘猿熟马驯”等等,部分术语还是对人物形象的比附,诸如以“心猿”、“金公”比
附孙行者;以“意马”比附白龙马;以“木母”比附猪八戒:以“黄婆”比附沙和尚;以“婴
儿”比附红孩儿;以“姹女”比附锦毛老鼠精等。这使得整个叙事文本警现出复杂、矛盾的
意义空间:一方面叙事者游戏笔墨、颠覆宗教的神圣,另一方面在文本整体架构上,却隐约
存在着宗教心性修炼的意蕴。在小说《两游记》的传播阶段,这种复杂矛盾的意义空间影响
到受众的理解。
27
关于《西游记》中花果山的创作原型,近年来随着洛阳、连云港两地花果山旅游资源开发的升温而争议不断。那么,究竟哪个花果山才是神话小说《西游记》的创作原型?
赞成花果山原型在洛阳者,从历史记载、自然风貌、民俗信仰等方面寻找了不少证据,还列举了1993年国家林业部将洛阳花果山命名为“洛阳花果山国家森林公园”,将连云港花果山命名为“连云港云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文件,以及中国民俗学会授予洛阳花果山“西游文化之乡”的相关证据,以此证明神话小说《西游记》中花果山的创作原型就是洛阳花果山。
赞成花果山原型在连云港者,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淮安人,就在连云港附近,描述的花果山场景,当以作者所熟悉的生活地为原型;且《西游记》中所写的花果山,在东胜神州大海中,而连云港古时就在海水边,因而,连云港花果山作为《西游记》创作原型,更有其合理性。
笔者认真阅读了洛阳、连云港关于《西游记》中花果山创作原型争议的相关资料,又多次到两地花果山实地考察,觉得中国民俗学会的专家教授们认为《西游记》中花果山创作原型在洛阳的观点更为让人信服:
专家:“在《西游记》、花果山与吴承恩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思维可能陷入了一个误区,过多的在吴承恩的籍贯与生活地区上考虑,而忽略了一些更为重要的因素——
“首先应该弄清《西游记》的来龙去脉。这部优秀的古典神话小说,公认的是吴承恩在采集丰富的取经故事和神猴故事基础上的二度创作。《西游记》主要写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高僧玄奘前往天竺(今印度)取经,17年后回国口述所见,和他的门徒们共同编写了<大唐西域记>,书中记述了玄奘西行天竺亲历一百余国的山川、域邑、物产、习俗,是一部写实性的地理专著。后来,他的门徒为了神话玄奘,又编写了<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描绘唐僧艰难西行的同时,穿插进了一些传说。玄奘取经历尽艰险的传奇经历,异国他乡鲜为人知的山川风情,为人们提供了提供了展开想象的广阔空间。到了南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书又把取经故事和大量的神话传说串连起来,书中开始出现猴行者的形象,这个猴子原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化身为白衣秀士,保护唐僧取经。猴行者神通广大,武艺高强,一路奋勇格杀妖魔鬼怪,使取经事业功德圆满。这部书已具备了《西游记》的雏形。明代初年,又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西游记平话>,神话传说愈加增多,猴行者的形象更加丰富。如说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钓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艰难困苦不知其几。其后又写到,花果山水帘洞有一个号称“齐天大圣”的老猴,偷了仙园蟠桃、老君丹药、王母仙衣,李天王奉命“引领十万天兵及诸神将”“与大圣相战失利”,后二郎神抓住了大圣,观音把它压入石山下,“饥食铁丸,渴饮铜汁”,后来唐僧取经路过此地,将大圣放出,“收为徒弟,赐法名悟空,改号孙行者。”唐僧还有两个徒弟,一个是黑猪精,一个是沙和尚……在平话故事广泛流传的同时,宋末明初还产生了多种取经杂剧,进一步丰富了西游故事的内容。所有这些都为小说《西游记》奠定了丰富的创作基础。 从唐代玄奘天竺取经(公元629年)到吴承恩写定《西游记》(约在公元1550年左右),前后经过了900余年的漫长岁月。“西游”故事的产生、流传和演变也可以划分出历史故事、佛教文学、平话、戏曲、长篇小说等5个阶段,这是一个历史向神话演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僧俗信徒、民间艺人和无名作者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为吴承恩的创作提供了基本素材和良好基础。因此,把《西游记》这一宏伟的神话小说的产生,完全归功于吴承恩无疑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小说《西游记》最初印行时,根本没有作者的名字。后来,一些书商还根据道听途说,把元代道人邱处机为游记《西游记》写的序,印在小说《西游记》的前面(邱处机曾随元太祖成吉思汗远征中亚细亚,写过一部游记《西游记》),以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误以为小说《西游记》是邱氏所作。直到清乾隆年间,著名学者钱大昕在<永乐大典>里发现了邱处机的《西游记》,方知与民间流传的小说《西游记》不是一回事,但究竟为谁所写,钱氏亦未弄清。民国时,大学者胡适读到<淮安县志>,看到其中一条,吴承恩,明朝贡生,著有《西游记》。胡适由此而写文章,把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定为吴承恩。从西游故事产生与流传的过程看来,吴氏之前900多年已有了西游故事,已有了唐僧、孙悟空等人物,已有了花果山、水帘洞等地名。因此,那种以作者的生活地来界定何处花果山为正宗花果山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
研 究
(原始材料汇编)
与明代产生的人多数古典白话K篇小说一样,《西游记》亦导源于历史中实有之事。小
说取材丁唐代僧人玄奘西行求法的史迹,在该小说正式成书之前,玄奘两游经历了故事的缘
起、传播和丰富的过程。在这一历时久远、塑造者众多的成书过程中,不仅有民间艺人的讲
唱言说,也有文人的踵饰其华,甚至还有宗教徒们的附会修撰,创造者们的这些改写百川汇
流,最终使两游故事由一次中土佛教史上的壮举,脱胎换骨为想象奇幻、意蕴丰富的文学叙
事。
玄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宗教家,是中十佛教唯识宗的开创者,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翻
译者,不过,最为tH=人所熟知和乐道的,是他去印度求取佛经的历险经历。在古代社会文化圈系相对封闭,人们惯于安土重迁,交通环境极其落后的条件下,玄奘白侦观三年秋起,“远
涉恒河”,“频登雪岭”,前后历经一十九年,广涉异域,从佛祖之地——天竺求取剑了“如
来之秘藏”、“释迦之遗旨”,最终返回东土。他的这一近乎“天路历程”的行为无疑可以称
之为一个奇迹,在世人眼中充满了神奇感,也延展了他们对陌生地理世界的想象。因此,从
玄奘两游故事的缘起之时,文本叙事便逐渐具有了神异传说的色彩。
关于这次两行求法的历史记录,首先是玄奘本人的各类表、启这样的零碎文本,简单勾
勒了自己西行的经历。此外,最早且最直观、完整的文本当属玄奘口授、弟子辩机撰文的《大
唐西域记》,以及其弟子慧立、彦惊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记
载玄奘西行所经过的各国的历史、地理、社会状况,既有各种迥异于中土的奇风异俗,也不
乏宗教传说的记载,特别是这些宗教传说,是以玄奘亲历发生之地的方式记载-卜.米。类似《犬
唐撕域记》卷一“迦毕试国”中,“城西南有比罗娑洛山,唐言象坚。山神作象形,故日象
坚也。昔如来在世,象坚神奉请世尊及千二百大阿罗汉。山巅有大磐石,如米即之,受神供
养”这样的叙述,反复出现,使得玄奘的西行求法之路,在读者眼中变成一次践履神迹之路,
玄奘本人乃至其西游经历因此有了神异的色彩。在稍后出现的玄奘传——《大唐大慈恩寺三
藏法师传》中,这种神化玄奘和西游故事的痕迹更加浓厚,玄奘得以度过漫长艰苦的取经历
程,与他作为信心执着的宗教信徒而时时受到神佛的保护,有莫大的关联。一次地理学意义
上的冒险故事,在玄奘弟子的夸饰敷衍下,呈现出一种趋向宗教理念宣讲的变形,取经路上
种种的磨难,遂被改写为神佛拯救的“幸运”,以强化信众的宗教信心。
这些讲述玄奘取经故事的历史文本,与后来的小说《西游记》也相去甚远。但作为小说
所依托的蓝本,还是为后来的文学叙事准备了条件。一是曲游故事中自马驮经的缘起。在玄
奘本人的表启一类的零碎文本中,尤可注意到的是玄奘屡次提及自己取经回来的过程是“白
19
马驮经”,《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有:“奘以贞观三年往游西域⋯⋯总获六百五十七部,并
以载于白马,以贞观十九年方还京邑。”又《谢御制三藏圣教序表》有:“搜扬三藏,尽龙宫
之所储;研究一乘,究鹫岭之遗旨,并以载于自马。还献紫宸。”等,白马驮经乃汉明帝时
事,洛阳白马寺由此得名,而玄奘多次讲述自己取经事用此典譬之,也就为后世文学叙事将
这两个历史事件的杂糅创造了条件;二是两游故事基本架构的建立。无论是《大唐两域记》,
还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都记录了玄奘西行求法之路所经过的西域诸国,在这两
个文本中,西域诸国虽还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描述,与后世的两游故事多为文学架空不同,但
遍历诸国度基本架构不变。中间所涉及的个别国家,仍为西游故事所承袭,如《大唐西域记》、
《法师传》中都有提剑的“两大女国”。三是神话色彩的讲述基调建立。玄奘西行求法,无
论是参与者还是记录者皆为佛教徒,其讲述肯定不同于一般旅行者所写的游记,超自然的宗
教叙述是其特点之一。故在《大唐两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两个文本中明显见
到宗教神话对玄奘西游这一地理旅行故事的渗入和改写,尤其是后者,多次记录了玄奘受到
畔申佛帮助的故事,《法师传》卷一有玄奘欠道野马泉,饥渴欲死,于沙中默念观音经,遂得
梦中神人指路,而获拯救事;卷三有玄奘于河上遇十余贼船,群贼欲以幺奘身体血祭突伽天
神,而玄奘受慈氏菩萨庇护,于是江面上“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
群贼折服受戒后,“风波还静”,以上都可以在后世的硝游故事上见到类似的影子。
除了以上三条要素间接影响剑后世两游故事的成型之外,历史叙述中的玄奘两行故事,
部分文本还直接深刻地影响到了文学的西游叙事,例如《法师传》中提及的《心经》故事。
这在下文中详细分析。
由唐末开始,一直到明中叶,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是唐僧西游脱离历史文本而逐渐向
文学的“西游”故事系统嬗变的过程,取经故事在宗教俗讲、造像、戏剧、平话、民间宗教
等渠道中传播,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嬗变过程不是单线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流传于受
众群体中的两游故事,并非干人一面,这些西游故事相互碰撞、相互借鉴,故事中的人物和
情节也因之渐次增加,逐渐发育成熟起来。
宋元时期,西游故事的传播开始向民间转移,寺院为了吸引民众,以“俗讲”的方式传
播一些宗教故事,以达到推,“宗教的目的,讲述玄奘两游的《人唐三藏取经诗话》便是其中
之一,由于《诗话》面向的接受群落,多为文化不高的俗众,故需要对原有的玄奘两游进行
加T和重写,删汰掉写实的游记色彩,而着意丁故事的奇幻效果和市井趣味,西游故事开始
脱离历史讲述的樊篱,具备了文学虚构的特点。《诗话》的奇幻效果是通过引入神魔形象和
神魔世界而达到的,与《两域记》和《法师传》不同,《诗话》中出现了人量的超现实的元
素,如火梵天王、王母、定光佛等神仙以及于深沙处横行吃人的深沙神、变成白衣妇人的白
虎精、九龙池处的九条馗头鼋龙等妖怪。最引人注意的,当然是《诗话》版本的西游故事对
玄奘一行人进行了改写,在取经队伍中安插了一位神通广大的猴行者,帮助玄奘降妖伏魔,
这标志着孙行者形象的正式出现。此外,《诗话》还通过对玄奘两行所经历的诸国进行重写,
变历史地理中实有之诸国为想象虚构的国家,如化用佛教中鬼子母之传说,创造出鬼子母国;
将玄奘西行时没有经过而仅提及一笔的“西大女国”,演绎为女人国,并编排了女人国国王
爱恋玄奘,却被其所拒的故事等,这也使玄奘西游由历史向超越的、想象的世界迈进了一大
步。
如果说《诗话》与之前的玄奘故事,还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只有玄奘本人了。但是即
便是这同一人物,由于改写者心态的变化,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历史中的玄奘坚韧执着,
几乎独自挑起了所有的困难,而《诗话》中的玄奘,既有大梵天王所赠的三宝:金环锡杖、
隐形帽、钵盂,又有猴行者的帮衬,更无危险艰难可言,所以,他的性格特点被削弱了不少。
不仅如此,在王母池处,玄奘竟然命令猴行者偷桃,看其所言,先是建议行者:“何不去偷
一个?”猴行者担心被捉,其又宽慰:“你神通广大,去必无妨。”至听见桃子落水时,则命
20
令道:“可去寻取来吃。”活脱脱一馋鬼的形象。由此也可知,在向民间传播的过程中,市井
趣味开始渗透到两游故事中来,并影响到了人物的塑造山。
宋元宗教人士向民间传播玄奘西游故事,并不J卜于俗讲这一渠道,还借助于造像艺术,
据已发现的资料,敦煌安两榆林窟保存有六幅两夏时期的唐僧取经壁画;杭州飞米峰龙泓洞
口,有据称成于元代的两组唐僧取经浮雕;广东省博物馆馆藏元代磁枕上,亦绘有唐僧取经图
等。出现于元代中期的《唐僧取经图册》更是以系列图画讲述了玄奘两游故事罾,包括了“张
守信谋唐僧财”、”毪虎国降大、小班”、“五方伞盖经度白蛇”、“玉玑夫人”、“释迦林龟子夫
人”、“六通尊者降树生囊行者”、“金顶国长爪大仙斗法”、“哑女镇逢I亚女大仙”、“明显国降
大罗真人”、“悬空寺过阿罗律师”、“过截天关见香因尊者”、“篮尉见摩耶夫人”、“白莲公主
听唐僧说法”、“万程河降人威显胜龙”等《诗话》中没有的内容。尽管有诸多不同,《图册》
早现出对玄奘两游进行神魔化重写的意图,却是与《诗话》一致的,两者另一相似的特点是
受到了密教的影响,毗沙|’J天-干都是作为玄奘的护法神山现的,《图册》中毗沙J、J天千护法
的作刚尤其明显,其地位相当于后期小说《两游记》中的观世音:落萨。
宋元时期,通俗文艺登上舞台,唐幺奘西游故事作为神鬼题材吲,自然也会得到诸如戏
剧艺术、说话艺术等通俗艺术门类的青睐。宋代之后,两游戏开始出现在戏剧舞台上,现在
已知的有,宋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唐三藏》、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两天取经》
等,这些戏剧或铺陈故事,或择其片段演绎之,其中情:1,最完整全面的,当属杨景贤的《西
游记》杂剧。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产生元末,较之作为宗教宣讲的两游故事,戏剧更注
重营造故事的吸引力,唐僧一行人,已经由普通凡人彻底过度到了神魔组合,唐僧陈光蕊乃
两天毗卢伽尊者托化,徒弟猴行者是大闹天空的“通天大圣”,“铜筋铁骨,火眼金睛”;朱
八戒是摩利支天菩萨座下的猪妖;沙和尚是玉皇殿前卷帘人将下凡。在故事架构上,孙行者
地位提高,几个主要的关口,收拿沙和尚、猪八戒、借铁扇、黄风山等,克服凼难的主角都
是他,说明西游故事的侧重点开始由唐僧取经向行者伏魔方向转变,其形态已经比较接近小
说《西游记》了。
杂剧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已完全市民化了,唐僧变成了一个性格软弱,屡受妖魔侵害,
需要神佛和徒弟时时加以保护的书生,遇剑火焰山阻隔,便叫:“来至火焰山,如何得过去,
行者怎生是好?”女人国被国干所迫,他先大叫“孙悟空救我。”见行者被缚,又对天大叫:
“谁来救我!”等,完全是一副无能、无主见的面孔;唐僧的儿个徒弟,则多少带有了点市
井无赖的色彩,女儿国唐僧脱难后,质问几个弟子为何不救自己,行者的答言可以说是这种
市井趣味的最生动的表现:
(唐僧云)行者,我们十分亏神天护持,脱了此一难。我且问你,我吃女王拿住,
你每三个怎的脱身?(行者云)师父,听行者告诉一遍:小行被一个婆娘按倒,凡心却
待起。不想头上金箍儿紧将起来,浑身上下骨节疼痛,疼出几般儿蔬菜名来:头疼得
发蓬如韭菜,面色青似蓼牙,汗珠一似酱透的茄子,鸡巴一似腌软的黄瓜。他见我恰
似烧葱,恰甫能忍住了胡麻。他放了我,我上了火龙马脊梁,直走粉墙左侧。听我有
个曲儿,唤做【寄生草】:
o《诗话》“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几处第十七”讲后妻谋害前妻之子事,曲说世情,也折射出市井之趣
味。
罾《唐僧取经图册》最早为日本学者矶部彰等学者所关注,并有相关研究文章,国内新近研究这一
图册与西游故事关系的,为曹炳建先生,参见其《((唐僧取经图册)探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8年第6期。
∞通俗艺术对神鬼题材的喜爱其来有自,宋耐得翁《都城纪胜》中讲:“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
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人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足也。”吴自牧
《梦粱录》中则说:“凡傀儡,敷演炯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
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皆指偏爱的主题中即有烟粉灵怪这一类神鬼故事。而元代杂剧中,神仙
道化、神头鬼面也是戏剧的两个重要题材,见明人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对元杂剧的分类。
21
【寄生草】猪八戒吁吁喘,沙和尚悄悄声。上面的紧紧往前挣,下面的款款将腰
肢应。我端详了半晌空侯幸,他两个忙将黑物入火炉,我则索闲骑白马敲金镫.
这种粗俗、黄色的描写也只有在市民意识占主导地位的通俗文艺中才能出现。
除了杂剧之外,其时还流传有一部《两游记》平话,平话《两游记》现已亡佚,不过仍
能从一些零碎的记载中见其人略。《永乐大典》尚存“梦斩泾河龙”一段故事;古朝鲜的《朴
通事谚解》中则载有“车迟国斗圣”的故事,在注解处详细介绍了西游故事的主要内容:“初
到狮陀国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经、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
孩儿怪,儿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水⋯⋯”这两部书都
将所摘择的故事来源标为《西游记平话》。透过这些零星的记载,可知平话《西游记》作为
叙事文学文本,故事情节基本完整,将其称之为小说的底本或蓝本,毫不为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间宗教的兴盛也推动了两游故事的传播,特别是明代,罗教、黄
天教、东西大乘教、弘刚教等民间教派叠次出现,这些宗教借助通俗文艺,传播教理,吸引
信众,因此在民间宗教教典——宝卷中留有大量的叙事文学素材,象《伏魔宝卷》谈的是关
帝;《二郎宝卷》则是二郎神;《东岳天齐宝卷》的主神自然尔岳大齐人帝;《地藏十千宝卷》
涉及佛教地狱的传说等等。但没有一个故事素材有唐僧两游故事这么大的影响力,明代主要
民间宗教,如罗教、黄天教、西犬乘教、红阳教、圆顿教等等的宝卷中都有两游故事的影子
∞。由于宝卷中的曲游故事是某些民间宗教宣传家用来传道的媒介,所以,呈现出宗教譬喻
的特点,这与在其他传播渠道中流行的两游故事是不同的。
玄奘西游故事由历史传记逐渐演变为叙事文学,这个过程呈现一个世代累积的特点,一
方面故事通过俗讲、通俗文艺等各种渠道散播于民间,另一方面不满足于接受已有故事的受
众,出丁这样或那样的目的,也会依据自己的期待视野进行发挥,改造故事以契合自己的思
想或审美需要,因此不同身份的作者,参与到加一F、改写中来,故事在I同有形态的基础上不
断地丰富,文学性、趣味性也不断增加。西游故事的基本形态便在这种动态的、复杂的传播
互动关系中逐步成熟。传播、接受的复杂性相应地造成了西游故事文本素材来源的多样化,
这主要体现在旧素材的复述改写,新文本和新文化因素的渗入等,尽管由于相隔久远,已无
法完全描述出这种文本互动的原貌,但仍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窥见一斑。
首先是文本的复述改写,《心经》故事是典型的一例。《心经》与西游记故事之间的缘分,
可上推至唐代。中国古代翻译《心经》的,较为有名的有两人:一是南北朝时期的鸠摩罗什,
另一个就是唐玄奘,唐玄奘所译《心经》,也即《两游》所引之《心经》,以文字简洁明晓而
广受欢迎,取代了鸠摩罗什《心经》大行天下,后人所用皆其译本。这也大概就是玄奘弟子
们把西游与《心经》编在一起的原因,《法师传》卷一讲述玄奘过“长八百余里”古沙河时: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孤影惟一,心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
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与衣服饮食之直。病者惭
愧,及售法师此经,因常诵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
①最早传播西游故事的是,正德年问出现的罗教,此后嘉万年间的黄天教祖师普明即以西游故事作为传教
之丁具。《佛说利生J,义宝卷》之“戊午开道普明如来归宫分第十三”“普叫佛,为众生,投凡住世;化男
身,性木子,四十余春;聚fE门,为结发,开花一二朵;长聘康,次聘高,两氏夫姻;有如来,再不知,已
为佛体;边塞.f:,受尽了,苦楚官刑;戊午年,受尽苦,丹书来召:大开门,传妙法,说破虚空;炼东方,
甲乙木,行者引路;炼南方,丙丁火,八戒前行;炼北方,壬癸水,沙僧玄妙:炼西方,庚辛金,白马驼
经;炼中方,戊巳土,唐僧不动;黄婆院,炼就了,五帝神通。”戊午为嘉靖三十七年。尽管其他的民间
宗教教派如弘阳教、东西大乘教等的产生,晚于小说《西游记》刊行的时间,但j£教派内部流行的西游故
事形态与小说小同,保留丫之前两游故事的形态,考虑到民间宗教相对封闭的体系和前后承袭的特点,认
为这些教派内的两游故事早于小说的出现,当不为过。
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
这一段文本素材,因其强调持经信心的神异效果,又刻意凸显《心经》祛邪的作用,为玄奘
故事的接受者所注意。
最先对这一素材进行复述和改写的,是唐末以后《独异志》等这样的笔记小说,复述
和改写的趋势,便是授经之人来由以及《心经》法力的神化,授经之人由《法师传》中感激
玄奘救助的“病人”,变为《独异志》中厕宾国道上“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却莫知由来的
老僧,《心经》的神奇效果一并夸饰为“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
但从叙事的内在逻辑上,《独异志》等志怪小说的《心经》故事与《法师传》差别不大,都
强调了《心经》在玄奘西游路上的保驾护航的作用。《独异志》的叙述后被收入《太平广记》
中,为世人所熟知。毫无疑问,这一授经的细:肖被小说《西游记》创造性地吸收进去哪。
至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心经》授受故事被编写者进行了较大改动,《心经》
的传授者不再是乞丐,或者来历不明的奇僧,演化成地地道道的神祗定光佛;《心经》保驾
护航的法宝功能也消火了,成了幺奘两行所要取的经典,且此经地位不凡,是在幺奘取得五
千四十八卷经文后,由定光佛单独传授的。正冈如此,这部经书才与玄奘历经艰辛所取得的
其他经书截然不同,“此经上达天宫、下管地府,阴阳莫测”,有着出类拔萃的神奇作用,东
土薄福之人,难以承受,故定光佛特意强调玄奘“慎勿轻传”,明代的民间宗教流传的某些
两游故事,强化了《诗话》的这种叙述结构,主要体现在《心经》取代了五千四十八卷其他
经文,成为唐僧一行取经的最终成果,“经历千山万水,受过若干魔障,方到雷音寺,取得
一卷《心经》,来到东士,超度亡灵,得升净十”;《诗话》中非凡俗薄福之人所能接受的《心
经》,则干脆被民间宗教命名为神秘的“无字经”。有意思的是,在小说《IHi游记》的结尾处,
有一段唐僧师徒取错经文的叙述,作者借此讽刺了某些佛教徒的贪财之相,但其中反复强凋
东土众生愚迷不悟,不识无字之经,与《诗话》系统的《心经》故事倒是颇有几分神似之处。
不排除《西游记》作者也承袭并改写了这一素材,纳入剑自己的小说文本系统中的可能性。
《心经》故事的传播及改写,使得这一情节具有了丰富曲折的变化,为小说《西游记》
的创作者处理这一西游故事的同有素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是新文化冈素、新文本的渗入。例如我们熟知的斩泾河龙、太宗游地府、陈光蕊江
流和尚等,起源之初皆属独立的故事系统,只是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渐次“参与”到西游
故事主体里来学。应该说这些新文化因素和新文本对于小说人物的产生、形象的丰富、情节
的拓展影响颇大。
两游故事从产生之日起,便置身子宗教信仰系统之中,记载玄奘西行的历史传记本属佛
教系统的文本,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虽已摆脱了历史传记,具有文学虚构的特点,
但作为俗讲,宗教色彩依然浓厚,密教成份的掺进是一显著的特点,沙和尚的前身深沙神是
从密教中实有的神祗——深沙大将借来的,唐中叶即有密教僧人不空所译的《深沙人将菩萨
仪轨》@,可知此一神祗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当然,《诗话》还吸纳了一些本士道教的
神仙故事,东方朔偷窃西王母蟠桃被讲述者改换了面目后,运用在了叙事中,说明宗教冈素
的杂糅,在西游故事传播的早期就已经开始了。元明之际的西游故事,本十道教强势介入,
宗教杂糅的趋势更加明显,以杂剧《西游记》为例,一些角色残留有密教的影响,如托塔李
天王,尚保持着“毗沙门天王”的名号,剧中朱八戒为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其身份
与猪的形象皆源出密教㈤;但道教化神祗出现的密度大大增加,如在道教侵润下而“转投门
o《太平广记》对玄奘两游的叙述,是牵合了《独异志》的《心经》故事及《唐新语》的摩顶松两迎玄奘
之事,后者亦出现在小说的文本中。
o见胡适《两游记考证》七。
@此一密教神祗与玄奘两游结缘,最迟不晚于中晚唐,同本入唐求法的僧人常晓云:“右唐代玄奘三藏远涉
五天,感得此神。此是北方多闻天上化身也。”,常晓开成三年到的中国,撰有《将来日录》。
@当然随着故事的发展和定型,猪八戒也转换了身份,其出身变成J,“知名”的道教护法神——天蓬元帅。
户”的沙和尚,由密教的深沙大将变成道教玉帝殿下的卷帘大将;再如铁扇公主首次出现在
杂剧中,她住的山,名日铁嵯峰或铁嵯山,使一柄铁扇子,重一千余斤,威力巨大,“着扇
扇翻地狱门前树,卷起天河水波”,这一形象并非作者独创,宋元时期道教雷法中有“铁扇
符”,由此符之描写可见当时一些道教徒信奉“铁支罗汉圣母”,此圣母居住于铁茶山,惯使
千斤铁扇,“扇山山崩,扇石石裂”,杂剧中铁扇公主这一新角色,应是化自于宋元道教神祗
“铁支罗汉圣母”。宗教神祗不断地进入西游故事,显然是冈为其超自然的神通力契合了神
魔故事对于角色的要求。这与其他类型小说的人物产生是截然不同的。
一些文本的进入和杂糅,对故事的人物形象向立体化发展也起到了推进作用,这在孙行
者形象的发展上体现得十分鲜明。从产生之初形象单薄的猴行者,到大闹天宫、降妖伏魔的
孙行者,其间经过了众多环节的加上塑造,其中一个环节是白猿精形象的糅入,唐传奇《补
江总白猿记》所记猿猴夺女之事,至宋时被敷衍成道士伏妖的故事∞,宋话本《陈巡检梅岭
失妻记》详细地叙述了白猿的来历,“且说梅岭之北有一洞,名日申阳洞,洞中有一怪,号
日白申公,乃猢狲精也。弟兄三人:一个是通大人圣,一个是弥天大圣,一个是齐天人圣。
小妹便是、泗洲圣母。这齐天人圣神通广大,变化多端,能降各洞山魈,管领诸山猛兽,兴妖
作法,摄偷可意佳人,啸月吟风,醉饮非凡美酒,与天地齐休,日月同长”这个两游故事系
统之外的齐天大圣白中公,后来被改写者加工,附会于猴行者的形象之上圆,创造出了杂剧
《西游记》中的通大人圣孙行者,他的家族也更加扩大,计有:“小圣弟兄姊妹五人,大姊
骊山老母,二姊巫枝祗圣母,大兄齐天大圣,小圣通天大圣,三第耍耍三郎”。白申公故事
的引入和创造性加一I==,使得此一时期的孙悟空形象“劣迹”更加卓著,既有《诗话》猴行者
盗取蟠桃的事情,也有向申公夺女之恶行,不仅如此,还添加了盗酒盗丹、闹反天宫之事。
作为主要角色,其“资历”之丰富,是之前西游故事中形象苍白的猴行者所雄相比的。
人物角色之外,新故事素材的进入,丰富了原有的叙事。兹举一例,两宋间,道教系统
中存在着搜山拿妖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主要为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固,自宋初李益据此题材
做《搜山图》,后世画家临摹、仿做者甚多,这一故事也逐渐剥离了宗教色彩,成为文学性
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朝代的二郎搜山故事虽小有差别,但不少题画的诗赞皆提及妖
怪的一方出现有猴精,诸如“洞中果熟邀申公,笑擎饯耸倾云腴”(元代文人叶森题宋于辉
画《搜山图》五十韵),“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明吴承恩《二郎搜山图歌》),
“狙公醉倒笑语扶,我冠堕地犹狂呼”(清赵执信《题搜山图》)等,天兵临近,大难临头,
猴精依然醉生梦死∞,与之对应的是二郎神率领天兵天将四处拿妖的气势,“清源真君颜如玉,
回宋道:}:撰《温太保传补遗》记载了一个故事:蜀口有一县,猴神作祟,县宰率兵杀猴神,破其庙。后县宰
解官而回,为猴神报复,猴神变作县宰之像,夺其家,占其妻妾。县宰后得龙虎山虚靖天师所助,请下神
祗温元帅降伏了妖猴。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似为《补江总记》与这一道士伏妖猴的故事杂糅改写而
成。
岱杂剧《西游记》的通天大圣孙行者,还保留着《诗话》的某些痕迹,如其所居住之地为“花果山”“紫云
罗洞”,显系“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乇”演化ffli来,可见两个系统故事合流的痕迹。关于白
猿故事文奉与孙悟空之间的渊源,可参考台湾郑明蜊《西游记探源》第_二章“人物与故事的演变”涉及孙
悟空的一节,另孙悟空形象的米源之一是亡J猿精,还有一旁证,明郑之珍《新编日连救母劝善戏文》中,
保取经僧傅罗卜西行求法的即足白猿精,也曾偷上母蠕桃,后被观音所派的神仙收服,劝其保护取经僧。
《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中两游故事就成熟状态向言,似应在小说《西游记》成型之前。对此故事年代
的判断依据,可参见苗怀明《两套西游故事的扭结》,《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l期。
@搜山故事的主角,清源真君二郎神之外,还有崇宁真君关羽,只足后者小甚流行罢了,据名号可知,此二
人皆道教系统之神祗,谳搜山故事的产生可能与当时兴盛的道教降妖术有关,《泰玄酆都黑律俄格》之“邪
精品”云:“今山源古树中,或狐猴蛇虺藏其中,年深亦能变化荚貌才男少女,迷惑移运。法官宜奏紫微天蓬,
用威猛大将剪除之。”搜山拿妖应足掌握符策、雷法之术的道七法官们的本职工作,而在道上命令天蓬大帅
属下众神拿妖时,有“(群妖)或飞走pq散。变化逃遁,即仰学谷入山,搜岩破穴,仔细搜寻,尽数峻食,无致遗
类。其有伏法受擒者,并奉犬仙法旨,押赴天-:It;狱,依律治罪”(《上清天蓬伏魔大法》)文字,其状与-N搜
山无异。
④现保留于故宫博物院的南宋佚名作者所绘《搜山图》残卷,也有猿精的形象,不过此猿精已被鬼卒捉拿,
24
玉冠上服笼绣襦。座中神色俨而厉,来征水衡校林虞。文身锦膊列壮士,挟弓持弹金头奴,
烈烈勇气增垣赫,飞捷喏奏传献俘。”(叶森题《搜山图》五十韵)这一场面的营构充满了戏
剧的张力。搜山故事后来被改写,与猿妖齐天大圣的故事扭结在一起,典型如杂剧《二郎锁
齐天大圣》锄,杂剧《西游记》中的天王父子搜山,也当视为此故事的另一版本,这可从天
王吩咐哪咤“与眉山七圣大搜此山”中见出,眉山七圣本为二郎随从之将。搜山擒妖题材的
出现,强化了西游故事中悟空本事的戏剧性冲突。
西游故事的成型阶段还可能有过一个宗教徒以性命修炼思想比附两游故事的环节。最早
揭橥两游故事有宗教心性意涵的,是明弘治、嘉靖年间的文人孙绪,其《沙溪集》卷一五有:
“释氏相传唐僧不空取经西天,西天者,金方也,兑地,金经所自出也。经来自马寺,意马
也。其日孙行者,心猿也。这同打个翻筋斗者,邪心外驰也。用咒拘之者,用慧剑止之,所
谓万里之妖一电光也。诸魔女障碍阻敌,临期取经采药魔情纷起也。皆凭行者驱敌,悉由心
所制也。自马驮经,行者敌魔,炼丹采约全由心意也”,此段文字至晚不会超过作者去世的
嘉靖二十六年,早于己知《两游记》最早的刊本世德堂本四十五年。西游故事是孙绪“阏与
方外友谈之flip而特意记录下来的,所谓方外之人,即是道教修炼之士。由此可知,《西游记》
正式刊行之前,故事形态在流传过程中得到了道教徒“青睐”,并建构起了故事人物一宗教
理念的隐喻系统。这也能从嘉靖万历之间的民间宗教处得到证明,如嘉靖年间之黄天教《普
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锁心猿合意马,炼得自乾。真阳火为姹女,妙理玄玄,朱八戒按南
方,九转神丹;思婴儿壬癸水,两意欢然,沙和尚是佛子,妙有无边。”再如万历初年之《普
静如来钥匙宝卷》:“唐僧非上两天去,一灵真性走雷音⋯⋯我性即是孙悟空,白马原来是我
意,八戒原来是我精,沙僧原来是我命,五气聚足发卷经。”
应该说,西游故事文本提供了宗教徒进行这种比附的可能:两游故事产生、发展、成熟,
人物和情节吸纳了大量的宗教元素,本就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取经队伍中同时出现猿猴和
自马,契合了宗教修炼体系中的“心猿”“意马”之说,杂剧《两游记》中便有“着猢狲将
心猿紧紧牢栓系,龙君跟着师傅呵把意马频频急控驰”,恰可说明故事角色和宗教术语之间
的对应关系,非是后人强行比附所致;孙行者盗取金丹之事,在宗教修炼之士眼中止是“休
纵心猿,盗了金鼎还丹,谩劳虚费”(元冯尊师《苏武慢》之一)这一修炼思想的反证:而
禅宗六祖慧能强调自心即佛,西天十万八千里,即是内心修炼所面临的“十恶八邪”,这种
化地理路径为内心理路的象征手法,影响了后世的宗教修炼者,元全真道士混然子有诗:“西
天十万八千程,要到端然坐是行。诗句唤同担板汉,点开脑后眼分明。”对于秉持这种“前
理解”的宗教徒来说,唐僧两天取经简直是一个进行宗教化阐释的天然素材。等等。
总之,新文本新故事素材的改写揉合,在叙事层面上极大地充实了西游故事的内容容量,
让角色的面目更加生动形象;在哲理成面上使西游故事的意蕴变得更加复杂,多少带有宗教
象征的特征。没有经过这一过程,就没有今天所见到的神魔小说《西游记》。
=:
小说《西游记》究竟出现于那一年,现已不可考,现存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刊本是明万历
二十年金陵世德堂刊刻的《新刻出像官板犬字两游记》,所以,以世德堂本《西游记》作为
西游故事定型的代表,当不为过。
挑于枪上。其故事性没有元明清题画诗赞形容的f富。
回(--fig神锁齐天大圣》收于明赵琦荚辑《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创作的年代不详,大致可以推断为万
历之前,杂剧中齐天大每保留J,猴精家谱,弟兄姊妹五人:大哥是“通天大圣”,老二是“齐天大圣”。兄弟
是“耍耍三邮”,姐姐足“龟山水母”,妹妹足“铁色猕猴”,与杂剧《西游记》相类,而截然不问于小说;
另杂剧中二郎神“俗姓赵名煜,幼从道士李班,隐于青城山。至隋炀帝,知吾神人贤,封为嘉州太守。郡
左有冷源-二河,内有键蛟,春夏为害。吾神持刀入水,斩蛟而l叶j。後弃官学道,白曰冲升,加哥神清源妙
道真君”,尚为道教系统中的神祗,也绝不同于小说中杂入民间传说的杨二郎形象,故可推知此故事所流传
之年代与杂剧《西游记》接近。
与之前的西游故事相比较,定型后的小说《西游记》最大的不同之处,乃在于成书者创
造性的改写。关于这个最后的创作者,从最初的“不知其何人所为”,到清人提出的丘处机,
再到今人力推的吴承恩等,说法不一而足。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创作者一定是一位颇具
才华,“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且生性诙谐的文人。否则,小说《西游记》很难让“底本”
故事蜕变为充满叙事魅力的文学精晶。
首先,创作者在进行最后的加工创造时,有自己的意义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主导了
小说形象的塑造和结构的处理。主要体现在孙悟空形象上,尽管到了通俗文艺阶段,孙行者
在叙事中的分量已经大为增加,但尚没有取代唐僧作为取经队伍第一主角的地位,而在小说
《西游记》中,孙悟空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主角,取经队伍中唐僧、猪八戒、沙和尚三人的出
身经历,皆以诗赞的形式粗陈其梗概,只有孙行者,创作者单独为他敷衍了七同文字,巨细
无遗地介绍他的出生、求法、除混世魔王、龙宫寻宝、地府除名,官封弼马温,大战李天王,
受招安封齐天大圣、偷桃偷酒偷丹,赌斗二郎神、老君偷袭成功,八卦炉中炼人圣,再反天
富,被压五行山等一系列经历,不仅在情一肖的丰富上远超杂剧,更重要的是创作者借助这么
人的篇幅,对这一妖猴形象进行了全新的重塑,把一个市升气流氓气十足的无赖猴子,转化
为追求自由、心高气傲的英雄。创作者增加学艺求法、龙富取宝、地府除名的情节,其目的
是为了渲染行者“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渴望打破一切束缚的自由精神;增加招安的
情节,意在表现天庭所代表的规范、教条和行者不服天地管束之间的矛盾,为后来行者偷酒
偷丹大闹天宫,做了一种合理的说明,从而消减了猴妖形象同有的贼性,赋予行者争取自由、
反抗束缚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在细二钳上,创作者对行者的言行也做了颠覆性的修改,杂
剧中的通天大圣,面对天兵,只会说:“小圣一筋斗,去十万八千里路程,那里拿我。我上
树化做个焦螟虫,看他鸟闹,把我媳妇还丁本国,我依旧入洞,顶上洞门,任君门外叫,只
是不开门。”形象猥琐而奸猾;小说中的孙行者面对天庭的玉帝如来,却敢于宣称:“冈在凡
问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大。凌霄宝殿非他有,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
此敢争先。”透露着掀翻天地一往无前的气魄。小说《矾游记》创作者花如此大的笔墨去重
塑行者形象,正体现了创作者把自己追求洒脱自由的情怀和浪漫的英雄情结,寄托在了这一
人物形象之上。
其次,创作者有自己一贯的叙事态度,即一种轻松幽默的游戏心态。这种叙事心态是如
此明显,以致于任何时期的阅读者都能真切地感到,即便是那些试图从中找到微言人义的阅
读者也不能否认小说的叙事者“其意虽游戏三昧,而广大具焉”(《西游真诠》尤侗序)。而
这也造成整个叙事文本始终保有一种谐谑笑虐的美学风格。通观小说,除了游离于叙事之外
的同目和诗赞,上至神佛帝王,下至山怪妖精,无一不是其调侃捉弄的对象:道教的最高神
祗三清,被猪八戒仍进茅坑;佛教最高神如来佛振振有词纵容徒弟收受贿赂;朱紫国国王被
含有马尿的药医好等等。小说中一个非常经典的情节处理,充分体现了创作者的游戏心态。
僧人授《心经》的片段是西游故事系统固有之素材,自《法师传》有此一说,后被文言小说
作家改写后,广为人所知,小说《西游记》承袭了禅僧授经的情节片段,除了将《心经》的
授予权交给了一位历史上实有的禅僧——鸟巢和尚,全文还摘录了《心经》的内容,有意思
的是,就在鸟巢禅师授予《心经》,并信誓日.旦地保证“若遇魔障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
害”之后,唐僧曲行路上即逢妖魔,创作者是这么叙事的:“三藏才坐将起来,战兢兢的,
口里念着《多心经》不题”,“路口上,那师父止念《多心经》,被他一把拿住,驾长风去了”,
三藏对《心经》护身的依赖和妖魔捉拿的轻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衬托出唐僧此举的滑稽
可笑。更妙的是,两件事情前后衔接,一个在十九同末,一个在二十回初,可谓鸟巢的保证
言犹在耳,《心经》立刻就表现出无用之物的本色,足以见出创作者是有意而为之的,其目
的就是颠覆传统《心经》授受故事的神圣性。正是这种游戏心态,使得叙事文本始终处在一
种笑谑诙谐的氛围之中,读者从中所见到是神佛身上折射出的人性的缺点,那些严肃神圣事
物的滑稽荒谬,正如胡适所言:“《西游记》所以能成世界的一部绝大神话小说,正因为《西
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之开口一笑,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过了。”
最后,创作者有一个能够驾驭各种素材,并夺其胎,换其骨,最终点铁成金的文心。故
其笔下故事链条首尾完整,叙事空间奇幻瑰丽、人物情:肖鲜活生动,充满了艺术之美。以人
物塑造为例,小说《西游记》与杂剧、平话比较起来,主要人物角色无甚变化,但角色内涵
之丰富却远逾之,皆为极富亲和力的艺术形象。孙悟空的尊性高傲本性刚强,猪八戒的贪婪
好色义有些呆气,唐三藏的软弱怯懦等,主要角色无一不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
各有身份。这得益于创作者抓住形象的某些特点进行夸张渲染的手法。如第三十二回“平顶
山功曹传信莲花洞术母逢灾”有一段猪八戒巡山的叙述:
那呆子入深山,又行有四五里,只见山凹中有桌面大的四四方方三块青石头.呆子
放下钯,对石头唱个大喏。行者暗笑道:“这呆子!石头又不是人,又不会说话,又不
会还礼的,唱他喏怎的,可不是个瞎帐?”原来那呆子把石头当着唐僧沙僧行者三人,
朝着他演习哩。他道:“我这回去,见了师父,若问有妖怪,就说有妖怪。他问甚么山,
我若说是泥捏的,土做的,锡打的,铜铸的,面蒸的,纸糊的,笔画的,他们见说我呆
哩,若讲这话,一发说呆了,我只说是石头山。他问甚么洞,也只说是石头洞。他问甚
么门,却说是钉钉的铁叶门.他问里边有多远,只说入内有三层.十分再搜寻,问门上
钉子多少,只说老猪心忙记不真。此间编造停当,哄那弼马温去!”
之前八戒屡次偷懒,皆被悟空变化捉弄,己颇为狼狈,又想耍心眼蒙骗唐僧孙悟空,此处,
叙事者特意设置了他对着人青石拿腔拿调地编假话的场景,对着石头编假话本就荒唐可笑,
在外人眼里“可不是个瞎帐”,而八戒却浑然不觉,斤斤计较于把谎话编圆,让人莫笑话自
己呆,这种反差产生了强烈的滑稽效果,八戒的呆气跃然纸上。如此精心地运用情节来打造
人物的个性,无论是宗教徒,还是民间艺人,都雉以做剑,只有倾心于叙事艺术感染力的文
人,方能有此文心文眼。
由丁成书者创造性的改写,《两游记》最终成为一个故事架构完整、情节生动有趣,人
物角色性格各异,拥有强烈叙事魅力的文学作品。这样一个文学精品的出现,标志着晴游故
事传播演化进程的上E式结束,开始进入以小说《西游记》为对象的文学传播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止因为小说《两游记》并非文人的独立创作,文本中还保留了一些旧有
的痕迹,最突出的是定型后的小说文本,在叙事之上附着了丰富的宗教文字:一些来自宋元
全真道十诸如紫阳真人张伯端、全真教教主王重阳,以及元代全真道十冯尊师等人所做的诗
词;一些出自宗教修炼体系的文本,像小说第三十六回悟空以月象变化为譬,阐明“先天采
炼之意”,实是张伯端《蟾光图论》相关论述的简约浓缩版;诗赞和目录中存在大量的宗教
术语,包括了“灵根”、“心性”、“悟彻菩提”、“元神”、“定心猿’’‘‘意马收缰”“尸魔”“木
母”“真性”“旁门~‘金木”“金丹”‘婴儿~‘禅心”“猿马”“刀圭”“法身”“元运”“车力”
“脊关”“外道”“水火”“炼魔”“黄婆”“寂灭”“七情~‘阴阳窍”“真如~‘姹女”“金公”
“灵元~‘猿熟马驯”等等,部分术语还是对人物形象的比附,诸如以“心猿”、“金公”比
附孙行者;以“意马”比附白龙马;以“木母”比附猪八戒:以“黄婆”比附沙和尚;以“婴
儿”比附红孩儿;以“姹女”比附锦毛老鼠精等。这使得整个叙事文本警现出复杂、矛盾的
意义空间:一方面叙事者游戏笔墨、颠覆宗教的神圣,另一方面在文本整体架构上,却隐约
存在着宗教心性修炼的意蕴。在小说《两游记》的传播阶段,这种复杂矛盾的意义空间影响
到受众的理解。
27
关于《西游记》中花果山的创作原型,近年来随着洛阳、连云港两地花果山旅游资源开发的升温而争议不断。那么,究竟哪个花果山才是神话小说《西游记》的创作原型?
赞成花果山原型在洛阳者,从历史记载、自然风貌、民俗信仰等方面寻找了不少证据,还列举了1993年国家林业部将洛阳花果山命名为“洛阳花果山国家森林公园”,将连云港花果山命名为“连云港云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文件,以及中国民俗学会授予洛阳花果山“西游文化之乡”的相关证据,以此证明神话小说《西游记》中花果山的创作原型就是洛阳花果山。
赞成花果山原型在连云港者,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淮安人,就在连云港附近,描述的花果山场景,当以作者所熟悉的生活地为原型;且《西游记》中所写的花果山,在东胜神州大海中,而连云港古时就在海水边,因而,连云港花果山作为《西游记》创作原型,更有其合理性。
笔者认真阅读了洛阳、连云港关于《西游记》中花果山创作原型争议的相关资料,又多次到两地花果山实地考察,觉得中国民俗学会的专家教授们认为《西游记》中花果山创作原型在洛阳的观点更为让人信服:
专家:“在《西游记》、花果山与吴承恩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思维可能陷入了一个误区,过多的在吴承恩的籍贯与生活地区上考虑,而忽略了一些更为重要的因素——
“首先应该弄清《西游记》的来龙去脉。这部优秀的古典神话小说,公认的是吴承恩在采集丰富的取经故事和神猴故事基础上的二度创作。《西游记》主要写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高僧玄奘前往天竺(今印度)取经,17年后回国口述所见,和他的门徒们共同编写了<大唐西域记>,书中记述了玄奘西行天竺亲历一百余国的山川、域邑、物产、习俗,是一部写实性的地理专著。后来,他的门徒为了神话玄奘,又编写了<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描绘唐僧艰难西行的同时,穿插进了一些传说。玄奘取经历尽艰险的传奇经历,异国他乡鲜为人知的山川风情,为人们提供了提供了展开想象的广阔空间。到了南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书又把取经故事和大量的神话传说串连起来,书中开始出现猴行者的形象,这个猴子原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化身为白衣秀士,保护唐僧取经。猴行者神通广大,武艺高强,一路奋勇格杀妖魔鬼怪,使取经事业功德圆满。这部书已具备了《西游记》的雏形。明代初年,又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西游记平话>,神话传说愈加增多,猴行者的形象更加丰富。如说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钓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艰难困苦不知其几。其后又写到,花果山水帘洞有一个号称“齐天大圣”的老猴,偷了仙园蟠桃、老君丹药、王母仙衣,李天王奉命“引领十万天兵及诸神将”“与大圣相战失利”,后二郎神抓住了大圣,观音把它压入石山下,“饥食铁丸,渴饮铜汁”,后来唐僧取经路过此地,将大圣放出,“收为徒弟,赐法名悟空,改号孙行者。”唐僧还有两个徒弟,一个是黑猪精,一个是沙和尚……在平话故事广泛流传的同时,宋末明初还产生了多种取经杂剧,进一步丰富了西游故事的内容。所有这些都为小说《西游记》奠定了丰富的创作基础。 从唐代玄奘天竺取经(公元629年)到吴承恩写定《西游记》(约在公元1550年左右),前后经过了900余年的漫长岁月。“西游”故事的产生、流传和演变也可以划分出历史故事、佛教文学、平话、戏曲、长篇小说等5个阶段,这是一个历史向神话演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僧俗信徒、民间艺人和无名作者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为吴承恩的创作提供了基本素材和良好基础。因此,把《西游记》这一宏伟的神话小说的产生,完全归功于吴承恩无疑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小说《西游记》最初印行时,根本没有作者的名字。后来,一些书商还根据道听途说,把元代道人邱处机为游记《西游记》写的序,印在小说《西游记》的前面(邱处机曾随元太祖成吉思汗远征中亚细亚,写过一部游记《西游记》),以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误以为小说《西游记》是邱氏所作。直到清乾隆年间,著名学者钱大昕在<永乐大典>里发现了邱处机的《西游记》,方知与民间流传的小说《西游记》不是一回事,但究竟为谁所写,钱氏亦未弄清。民国时,大学者胡适读到<淮安县志>,看到其中一条,吴承恩,明朝贡生,著有《西游记》。胡适由此而写文章,把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定为吴承恩。从西游故事产生与流传的过程看来,吴氏之前900多年已有了西游故事,已有了唐僧、孙悟空等人物,已有了花果山、水帘洞等地名。因此,那种以作者的生活地来界定何处花果山为正宗花果山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
- 上一篇:浅谈花果山与西游文化

 中文
中文 ENGLISH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