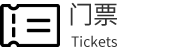洛阳花果山道教文化刍议
洛阳花果山道教文化刍议
扈耕田
花果山又名女几山,为河洛地区重要山系熊耳山的三大主峰之一,居洛阳以西九十公里宜阳境内洛河南岸。作为千年帝都洛阳京畿之地的道教名山,其丰厚而多元的意义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但对这一问题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研究,本人不揣谫陋,试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花果山在洛阳周边道教名山中的意义
洛阳作为千年帝都,其形胜之处,前人总结为山河拱戴。这里的河容易理解,黄河、伊、洛、瀍、涧是也。而山则指北部的王屋山、邙山、东南的嵩山、西南部的伏牛山、熊耳山等。在以道教文化为基础的洛阳都城文化圈中,王屋山、嵩山,意义尤其重大。前者不仅称为王屋,而且山上有天坛;后者则被称为天室,后又列入五岳之中岳。它们南北列张,势如洛阳之两翼。而上溯洛水,在其西部的第一座道教名山,则是花果山。我们考察一下,王屋山距离今日洛阳约110 公里,而嵩山、花果山均约90公里。如果考虑到古代洛阳定都的夏商及汉魏等朝代,更偏于洛阳的东部,则花果山与其之距离大约在130公里左右。可以说花果山与王屋山、嵩山,恰如洛阳盆地的三只鼎足。由于其位于洛阳以西洛河上部沿岸,虽名声不若嵩山、王屋之大,但亦自有其独特的地位,为帝都西部之巨镇。清代吕履恒《女几山》一诗称其为“一柱砥三川”。三川是古代对洛阳的称呼,因此吕履恒的这句话,正是看出了女几山在洛阳的意义。而从名称上来看,女几山又称天几山。李贺《昌谷诗》有云:“高眠服玉容,烧桂祀天几。”天几、天坛、天室构成一个完整的以“天”来全名的完整系列,可见花果山在洛阳周围名山中的特殊意义。
正因如此,花果山在道教典籍中,有着很高的地位。首先,花果山被称为西岳华山的佐命之山、中岳嵩山之副。唐代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有云:“西岳华山,岳神金天王,领仙官玉女七万人,山周围二千里。地肺山、女几山为佐命。”而泰山岱庙所存的五岳真形图碑中有云:“中岳嵩山,在西京河南府登封县,是寇谦真人得道之处,女几、少室二山为副。”由此可见,女几山有时被称为西岳华山的佐命之山,有时又被称为中岳嵩山之副。处于两京之间的女几山,在道教文化史上实有着挽合西岳、中岳的重要意义。
其次,花果山在宋代被称为道教的福地之一。唐代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司马承祯的《天地宫府图》列道教七十二福地,均无女几山。而宋代李思聪《洞渊集》卷四所列道教福地中则有云:“第六十六福地女几山,在三峡口。第六十七福地少室山,在邓州南阳县。”这里明确地将将女几山列为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有别于唐代杜光庭、司马承祯的记载。然而关于女几山所处的方位,却被置于三峡口。我以为这里可能有误。原因有二。第一,这里在叙述少室山时,就将其地点误归于邓州南阳县了,因此在叙述女几山时,亦有可能有误。第二,这里将女几、少室并置,显然受到了五岳真形碑中将女几、少室作为中岳嵩山之副的影响,其所指的女几亦应当是洛阳的女几山,而不是四川的女几山。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宋代时,花果山曾被誉为道教的七十二福地之一。综合李思聪、司马承祯、杜光庭的相关记载,道教的洞天福地多集中于南方,北方则以洛阳附近为最多,列入其间的共有王屋山王母洞(十大洞地)、嵩山洞(三十六小洞天)、北邙山、缑氏山、少室山和女几山(七十二福地)。
再次,花果山曾与青城山、娥眉山等道教名山并称。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金丹》篇记载天下名山,云“有华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长山、太白山、终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犊山、安丘山、潜山、青城山、娥眉山、绥山、云台山、罗浮山、阳驾山、黄金山、鳖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盖竹山、括苍山”。这里将女几山与华山、青城山等名山并称,可见花果山在当时的地位。
另外,《云笈七签》卷一百四《纪传部·传二·太清真人传》云:“按张天师述《老君本纪》云,老子幽演讫,乃与文始先生游此赤城上虞山,过女几、鸡头、天柱、太白山。”此处云老子出关所经之女几山,极可能是今天洛阳的花果山。以此山正处于洛阳向西至灵宝函谷关之洛河水路及大道南。
二、花果山道教文化的特点
花果山作为道教名山,花果山有着显著的特点。
首先,花果山是洛阳周边重要的养生修道圣地。作为魏晋神仙道教的代表人物,葛洪非常重视“名山”在金丹修炼中的意义。他说:“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为此也。”列上述女几山等名山,称之曰:“按仙经,可以精思合作仙药。”他又指出:“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难,不但于中以合药也。若有道者登之,则此山神必助之为福,药必成。”因此花果山为历代仙真所喜爱的修道之所。据文献记载,晋代名士孙登、张轨、皇甫谧等皆曾至此修炼。此已为今人所熟知。而《太平广记》卷第七神仙七所载马鸣生在女几山修道之事,则今人多有不详,特录于下:
马鸣生者,临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贤。少为县吏,捕贼为贼所伤,当时暂死,忽遇神人以药救之,便活。鸣生无以报之,遂弃职随神。初但欲治金疮方耳,后知有长生之道,乃久随之,为负笈,西之女儿(即女几)山,北到玄丘,南至庐江,周游天下,勤苦历年,及受《太阳神丹经》三卷归。入山合药服之。不乐升天,但服半剂为地仙,恒居人间。不过三年,辄易其处,时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舍,畜仆从车马,并与俗人皆同。如此展转,经历九州岛,五百余年,人多识之,咸怪其不老。后乃白日升天而去。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花果山和西游记的联系,人们可能以为花果山的主体文化应为佛教。其实,花山庙、岳山庙、七峪宫等供奉的均为道教的神灵。就其建筑规模而言,花果山一带应当是古代洛阳周边道教宫观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其次,花果山是一座女仙之山。作为道教名山,花果山必然是仙人所集之处。故它被称为仙山。而在众仙之中,他有一个显着特点便是女仙极多。从其山名由来来看,它原名姑媱山。《山海经》《中次七经》载:“又东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蘨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正因如此,此山又名化姑山。宋代《太平寰宇记》称此山为花果山,可能是化姑山之音讹,而因为后来《西游记》的影响,成为了今日的正名。
依《山海经》之说法,此山不仅是帝女所化,且其所化之草服用之后能使女姓更加美丽妩媚。故此山与女仙关系极其密切。最为著名者,有女几、彭娥、兰香等。
女几之事,见于汉代的《列仙传》。因字形之近似,亦有写作女丸者。原文如下:
女几者,陈市上沽酒妇人也,作酒常美。遇仙人过其家饮酒,以素书五卷为质。几开视其书,乃养性、交接之术。几私写其文要,更设房室,纳诸年少,饮美酒,与止宿,行文书之法。如此三十年,颜色更如二十。时仙人数岁复来过,笑谓几曰:“盗道无私,有翅不飞。”遂弃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玄素有要,近取诸身。鼓、聃得之,五卷以陈。女几蕴妙,仙客来臻。倾书开引,双飞绝尘。
这又是一个令女子变得年轻美丽的故事,从中可以女看出瑶姬传说的影响。至于书中说女几不知所终,其实是升仙了。
不过,山名女几山,另有一种说法。山上有兰香女神庙,唐诗人李贺有《兰香女神庙》。 这位兰香女神,世人多以为即《太平广记》中所载之杜兰香,其实这并不可靠。《古今图书集成》女几山部汇考引《广与记》曰:“白兰香女神上升遗几于此。”可见此山的兰香女神是白兰香。此山为其升仙之地,而她飞升之时,遗几于此,故山名女几。
到了晋代,又有了彭娥的传说。南朝宋刘义庆撰写的《幽明录》之《彭娥》篇载:
晋永嘉之乱,郡县无定主,强弱相暴。宜阳县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余口,为长沙贼所攻。时娥负器出汲于溪,闻贼至,走还,正见坞壁已破,不胜其哀,与贼相格,贼缚娥,驱出溪边,将杀之。 溪际有大山,石壁高数十丈。娥仰天呼曰:“皇天宁有神不?我为何罪,而当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开,广数丈,平路如砥。群贼亦逐娥入山,山遂隐合,泯然如初。贼皆压死山里,头出山外。娥遂隐不复出。 娥所舍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土人因号曰石鸡山,其水为娥潭。
尽管这一故事发生地目前存在争议(或以为发生在江西宜春,历史上亦曾名宜阳),但作为民间故事,彭娥在花果山受到了尊崇,她俨然成为了花果山的女仙之一。人们在山下修了女几祠。明人顾达在《谒女几祠》中赞曰:“当时汲器真有灵,化为巨犹像形。至今樵客或时见,欲往从之应未能。”
而唐代刘禹锡《三乡驿楼伏观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开元天子万事足,唯惜当时光景促。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更将此处视为唐玄宗创作霓裳羽衣曲时激发其灵感之地。又《逸史》云:“罗公远天宝初侍玄宗,八月十五日夜,宫中玩月,曰:‘陛下能从臣月中游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掷之,化为一桥,其色如银。请上同登,约行数十里,遂至大城阙。公远曰:‘此月宫也。’有仙女数百,素练宽衣,舞于广庭。上前问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记其声调,遂回桥,却顾,随步而灭。旦谕伶官,象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可见唐玄宗当时是在恍惚间看到女几山有众仙女跳舞而得以创作霓裳羽衣曲的。
从化姑山到女几山,再到因字体形似而误称的女儿山,花果山都和女仙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再次,花果山是中原齐天大圣信仰中心。洛阳花果山中史籍所载最早的花果山。洛阳花果山之名称,最早见于北宋《太平寰宇记》:“寿安县岳顶山在县西南,又西为花果山。”《太平寰宇记》为宋太宗赵炅(939年-997年)时的地理总志,由乐史所撰。则其时代为北宋前期。作为地理书,该书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就笔者所见之文献,这是古代史籍中最早出现的花果山。此后,花果山的出现就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该书载秀才即孙悟空语曰:“我不是别人,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世多以为宋刊,鲁迅认为作者或为元人。相对于《太平寰宇记》而言,其时代晚了许多。因此作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前唯一见于记载的花果山,《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作者在创作时有可能受到了宜阳花果山的影响。而明代《西游记》中花果山的名称则是直接沿袭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伊洛汝颍乃至整个中原地区,曾经产生了有着广泛影响的齐天大圣信仰。这一信仰可能早于《西游记》的成书,但《西游记》对其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洛阳民间称齐天大圣孙悟空为西佛,而花果山被称为“西佛发祥之区”。嵩县城关镇王庄村头宫庙现存《头宫庙重修碑记》(清 乾隆四十四年)载:“嵩宜接壤,有花果仙山,为西佛发祥之区。越花果山东,东去嵩治六十里,遥与阴山□□沟,旧有西佛下院,名之曰头宫庙。”而花果山现存碑刻云花山庙一带,群峰“端拱对峙”,如大圣与人“谈取经时神通变化事”,更被称为“大圣道场”之所在。花果山俨然成为了中原齐天大圣信仰的中心。流风所被,西游文化深深渗入当地文化及生活的肌理之中。这里不仅有水帘洞、高老庄等地名,有花山庙、七峪宫中的大圣殿,而且民间普遍奉祀齐天大圣,有丰富的大圣显灵传说,有当今唯一存世的《大圣经》。一年一度的花山庙会,更是齐天大圣信仰文化的集中展演。花果山浓郁的西游文化与齐天大圣信仰,不仅反映着《西游记》作为文学经典的深远辐射力,而且反映着民间对齐天大圣斩妖降魔、除暴安良行为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信仰,更与福建、台湾等地的齐天大圣信仰一脉相承,是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花果山和《西游记》的联系,人们可能以为花果山的主体文化应为佛教。其实,花山庙、岳山庙、七峪宫等供奉的均为道教的神灵。就其建筑规模而言,花果山一带应当是古代洛阳周边道教宫观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而所谓的“西佛”齐天大圣,也是道教神仙之一种。
最后,花果山是一座有着浓郁文化积淀的道教文化名山。在中国诗歌史、艺术史、政治上都有有着一定的意义。
花果山景色雄奇秀美,为历代名人流连忘返。《水经注》卷十五云:“渠谷水出宜阳县南女几山,东北流迳云中坞,左上迢递层峻,流烟半垂,缨带山阜。”唐代诗人刘禹锡《九华山歌并序》称:“昔余仰太华,以为此外无奇;爱女几、荆山,以为此外无秀。” 美景令人应接不暇。故历代名人雅士多有慕名前来,并欣赏题咏。据笔者初步搜集,历代题咏之作已有近百篇。如唐代著名诗人羊士谔《过三乡望女几山,早岁有卜筑之志》云:“女几山头春雪消,路傍仙杏发柔条。心期欲去知何日,惆怅回车上野桥。”唐代若耶溪女子李弄玉《三乡诗》云:“昔逐良人西入关,良人身殁妾空还。谢娘卫女不相待,为雨为云归此山。”均表明了欲归隐此处的心态。
刘禹锡笔下的花果山又是霓裳羽衣曲(舞)的发源地。其《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云:”开元天子万事足,唯惜当时光景促。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仙心从此在瑶池,三清八景相追随。天上忽乘白云去,世间空有秋风词。”霓裳羽衣曲是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据《历代崇道记》载:“《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荐献于太清宫,贵有异于九庙也。”可见其在唐代宫廷音乐中的特殊地位。
花果山居于两大都城洛阳与西安间交通要道之水陆要冲附近,其对岸的三乡驿,即是由洛河水路与通往陕州的陆路之交汇点。唐代名相裴度讨伐淮西之乱,曾于此刻石明志。白居易观裴度之刻石,深有感触,为诗曰:“何处画功业,何处题诗篇。麒麟高阁上,女几小山前。”清人吕履恒在《女几山》一诗中亦对花果山文化意蕴及战略意义有高度概括:“周韩轇轕地,设险重西偏。”
历史上,花果山曾是前凉国国王的龙兴之地。《晋书·张轨传》说:“张轨与同郡皇甫谧善,隐于宜阳女几山。”女几山是张轨出仕之前的隐居之地。《晋书·张轨传》载,建兴二年(314),张轨病重,上书朝廷,请求“欲避位,归老宜阳”。但未待朝廷答复而病故,其子张寔继承父职。西晋灭亡后,北方处于大分裂时期,张寔建立凉国,后来张轨被尊为凉国太祖。从张轨起,张氏家族前后统治西凉地区长达76年,史称“前凉”。在五胡十六国时期,随着西晋晋室南迁,中原地区汉文化呈现出荒漠状态,而张氏在西北地区建立的前凉政权,却为汉文化在西北地区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以上简单探讨了花果山道教文化的若干问题。由于学识有限,所论尚有欠缺及不严谨之处,诚望博雅之士多提宝贵意见。
扈耕田,男,河南宜阳人。文学博士,洛阳理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社会科学处副处长、洛阳市河洛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现为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赋学会理事、华夏老子学联合会常务理事、洛阳辞赋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洛阳诗词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河洛文化、牡丹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主持教育部及省厅级项目《洛阳及周边地区道教碑刻整理与研究》、《明清河南文化世家研究》、《历代牡丹谱全编》、《吕维祺全集》、《河洛文化与一带一路》等项目30余项。先后在《民俗研究》、《史学月刊》、《中国道教》等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河洛文化论衡》、《煌煌京洛十三朝》、《历代咏洛赋评注》、《河洛文化与一带一路》等著作10余部。曾获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各1次,地厅级科研成果奖12次,并获河南省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洛阳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称号。
- 下一篇:岳顶山麓云盖寺

 中文
中文 ENGLISH
ENGLISH